《猶太警察工會》中的空間政治與彌賽亞主義
時間:2021年02月27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邁克爾·夏邦的《猶太警察工會》是一部或然歷史小說和偵探小說,其背景是一個假想的歷史空間,即二戰期間美國在阿拉斯加的錫特卡建立的一處歐洲猶太難民聚居點。故事詳細記述了主人公通過對一起神秘謀殺案的調查而最終發現的政治陰謀。這部小說實際是一部“空間故事”,其中有各種各樣的邊界跨越與疆域控制,從中能夠看出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正統猶太人與世俗猶太人之間的復雜關系以及當代以色列國的縮影。本文專注小說中的空間因素(特別是阿拉斯加猶太人聚居點的孤島意象和島上的開戒界域),探索它們在猶太身份的形成與交涉中所起的作用,并在此基礎上挖掘深藏其中的意識形態信息,包括作者對現實中的以色列國的諷喻性暗指以及對猶太復國主義和彌賽亞主義所持的復雜態度。
關鍵詞:邁克爾·夏邦;或然歷史小說;猶太身份;猶太復國主義;彌賽亞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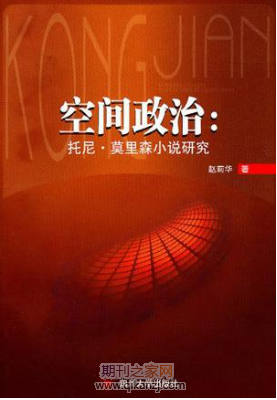
引言邁克爾·夏邦(MichaelChabon,1963-)是新一代美國猶太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寫作體裁和技法多種多樣,其中包含科幻、偵探、歷史、探險等元素。盡管作為第四代移民,夏邦更加認同自己的美國人身份,而非猶太族裔身份,甚至曾在采訪中坦承“我們無法進入傳統猶太世界,我們不懂意第緒語,也不懂希伯來文化里的秘密”①。然而有趣的是,他的多數作品仍然是以猶太人為主人公,探討的核心問題之一也依然是猶太民族的身份。《猶太警察工會》(TheYiddishPolicemen'sUnion,2007),又譯作《消逝的六芒星》,是夏邦的代表作。該書既是一部猶太題材的或然歷史小說(alternatehistoryfiction),也是一部典型的硬漢式偵探小說。
作者以歷史上并不存在的阿拉斯加猶太定居點為背景,講述了猶太警探蘭茲曼調查一樁神秘兇殺案,由此一步步發現背后的政治陰謀的故事。小說的靈感最初來自夏邦早先的一篇文章《幽靈國度旅行指南》(GuidebooktoaLandofGhosts,1997),而后幾經重寫和修改,最終在2007年5月得以成書出版,隨即獲得極大關注和廣泛好評,并接連斬獲星云獎、雨果獎、軌跡獎、斜向獎等諸多重要的文學獎項。阿拉斯加:行將終結的猶太國度在這部小說的想象歷史空間中,以色列建國僅僅三個月即在阿以戰爭中遭到慘敗,并于1948年滅亡;而在此之前的美國,由于猶太裔美國人的大力游說,加之極力反對猶太人移民阿拉斯加的眾議員安東尼·戴蒙德(AnthonyDimond)意外遭遇車禍身亡(此即該書的歷史分叉點)②,美國國會于1940年順利通過了《斯萊特里報告》(SlatteryReport),將阿拉斯加的錫特卡(Sitka,Alaska)的一部分土地辟為聯邦特區,作為歐洲猶太人的臨時定居點,期限為60年,這一決定使大量猶太人免遭納粹迫害的厄運。
小說的故事背景是在當下(21世紀初的某年),距離所謂“回歸”(管轄權移交)只剩下區區數周時間。屆時,錫特卡作為聯邦特區的臨時地位將宣告結束,該定居點的土地將被美國政府收回,居住于此的猶太人將不得不再次面臨四處流散、尋找家園的命運。與多數或然歷史小說著重表現歷史上的關鍵轉折點不同,《猶太警察工會》把關注重點放在歷史轉軌后的當下———小說對后大屠殺時代猶太人的心理創傷進行了重新想象,審視他們在嚴酷環境中的生存策略。
事實上,猶太民族在現代人類歷史上的坎坷命運一直是或然歷史假想的常見母題之一,然而與多數此類小說以同情筆調刻畫猶太人(如菲利普·羅斯的《反美陰謀》)所不同,夏邦對書中的部分猶太人進行了頗為負面的刻畫。小說開篇即是一個頗為神秘的犯罪現場———國際象棋天才、猶太青年孟德爾·施皮爾曼在柴門霍夫賓館被謀殺身亡,這家廉價賓館是一處“破敗不堪的住所,以世界語的創始人命名,一開始就象征了失敗的烏托邦愿景,見證猶太人的錫特卡被美國政府收回”(Witcombe,2016:45)。值得注意的是,在施皮爾曼的尸體旁邊還有一個棋盤,上面有一盤未完成的棋局。
主人公蘭茲曼警探攜手老搭檔波克對此案展開調查。此時的蘭茲曼正值落魄潦倒之際———之前因醫生懷疑胎兒的染色體異常,他誤將正常的孩子放棄,妻子因此離異而去,留下他整日酗酒、頹 廢度日;更為糟糕的是,距離阿拉斯加被美國政府收回僅僅只有6周時間,蘭茲曼很快將失去工作,不得不同其他猶太人一樣另謀歸宿,但他依然下定決心要將案情查個水落石出。猶太空間:孤島意象與開戒界域通常認為,就敘事技法而言,情節鋪陳并非夏邦在小說創作上的強項和優先考慮,相反,他的寫作主要是“通過明確具體的細節、準確呈現的場景、細致入微的人物性格發展來積聚力量的”(Dubrow,2008:145)。
這些特征在《猶太警察工會》中尤為明顯,特別是作者對空間的塑造與駕馭———“盡管文本結合了大量與已知文學體裁相關的修辭手段,但夏邦小說的最成功之處,是表現出一個想象的猶太空間其內部是如何運作的”(Witcombe,2016:31)。在這部小說中,我們確實能夠找到大量的空間元素以及各種邊界跨越與疆域控制的題材(例如引人入勝的環境描寫、主人公歷險過程中的物理位移、精心布置的棋局等)。這些元素和題材,大多與書中的猶太身份這一主題密切相關,即“空間的復雜本質是整個敘事的核心部分,對于在一個后現代的、編造的世界中探索猶太身份至關重要”(Anderson,2015:87)。
事實上,或然歷史小說這一文類本身即具有荒島小說中“空間故事”的諸多特征,這在猶太題材的小說中尤為明顯———作家頻繁利用“島嶼”作為假想歷史中的猶太國度所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歷史上確曾出現過此類提議(如馬達加斯加、塔斯馬尼亞以及阿拉斯加半島);另一方面,“孤島的隱喻十分適合猶太人本質上(相對于非猶太人)的他者身份”(Rovner,2011:145)。
《猶太警察工會》的故事確實給讀者一種強烈的隔離感———書中《斯萊特里報告》在國會通過時,各方均做出一定妥協,其中就包括對猶太移民行動范圍的限制,正如他們的護照封面上標明的:“你哪兒也去不了。你不能去西雅圖,不能去舊金山,就連阿拉斯加的朱諾或凱奇坎也去不了”(31)。伴隨這種隔離感的,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悲涼末日感。考慮到當時的時代背景(即猶太人在阿拉斯加的居住地位行將結束),這也極為正常———書中由美國政府先期派來的“阿拉斯加管轄權移交委員會”被當地人戲稱為“喪事協會”,他們將要接手的工作就像“準備和監督一場歷史葬禮,以最終將這個猶太人的特區送進歷史的墳墓”(62)。
此類用詞都是這個猶太國度行將死亡的隱喻。如何將潛藏的文學空間結構轉換成清晰直觀的地圖意象,多年來困擾著眾多英美文學研究者(郭方云,2019:39)。開戒界域實質上是一種權力角逐的空間實踐———在界域內,正統派猶太教徒有其自身的宗教法規,它們同外部的官方法律和世俗秩序形成對立。糟糕的是,故事中開戒界域的設置并不僅僅出于宗教目的,還為了犯罪便利———維波夫島上有一位專職的“邊界大師”,其“特長就是用成排的細繩在人們的住所四周圈出疆域,好讓他們在安息日可以開展非法行動,據稱這樣就不會違反在神圣節日必須休息的諭令”(Kravitz,2010:104)。
換言之,如此一來,這些猶太人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擺脫教義約束,即使在休息日也照樣收租放租、敲詐勒索。夏邦對這種自欺欺人的做法非常憎惡,他認為這“顯然是想執意欺瞞上帝、躲避他的律法,已然淪為一種騙局”(Kravitz,2010:104)。作為外來的闖入者,蘭茲曼警探是一個不信教義的世俗猶太人,“對他而言,天堂是個假貨,上帝是個字眼,靈魂頂多只能算是電池的電量”(144)。但此人一心伸張正義、追查命案真兇,甚至想在維波夫島的開戒界域內重樹世俗社會的法制與秩序。
他的行為,代表了界域外的另一種猶太性,正如安德森所言,“蘭茲曼作為世俗錫特卡的一名警察,似乎想要求所有的錫特卡居民都遵從政府的世俗權力,而維波夫派猶太人效忠的卻是宗教勢力的法則,這就削弱了世俗主義的公民原則”(Anderson,2015:100)。這兩者之間巨大的矛盾沖突,構成了敘事向前推進的張力。事實上,在維波夫島上的開戒界域里,處處充斥著對猶太身份、猶太人—非猶太人關系的爭論,可說是一個“爭奪異常激烈、象征意義豐富的身份交涉的空間”(Witcombe,2016:30)。在夏邦眼里,這樣一個“集體的猶太身份……既不取決于國家主權,也不取決于任何形式的真正的政治或領土控制”(Mann,2012:146),而是一種思想意識與生存狀態。
猶太人聚居點:以色列國的縮影《猶太警察工會》中的空間與疆域,其物理背景設定在阿拉斯加,然而跟真實的以色列之間卻構成了一種微妙的互文關系———盡管小說所描繪的是一個以色列輸掉阿以戰爭、已經不復存在的假想世界,“猶太人被完全推到了歷史的另一條軌道上”(Henderson,2007:254),但書中對以色列國的各種影射卻若隱若現,讓人始終能夠感覺到它的存在。首先,前面討論過的開戒界域,除了作為身份塑造與交涉的載體之外,還暗含著強烈的政治信息,它其實是一個“如同以色列一般微觀的地緣政治實體,其中各種各樣的觀念視角都在極力參與空間的界定”(Anderson,2015:100)。
我們從小說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對以色列國和正統派猶太教徒的態度:(1)通過對開戒界域本身的負面刻畫,夏邦表達了對現代以色列國治理方式的質疑,特別是對以色列領土政策的批評,即“對維波夫派通過意識形態構建的景觀進行批判……暗中是在指責現代以色列,表明其地緣政治邊界的構建本身,只不過是企圖建造猶太身份的‘鄉土建筑’”(Anderson,2015:103);(2)通過對維波夫派猶太人的負面刻畫,夏邦明顯是在對正統派猶太教徒提出批評,尤其是他們對國家政策的過度干預,即“由于議會制度的奇異,這些人對以色列的國家政治與財政預算所具有的異乎尋常的影響力”(Kravitz,2010:103)。
其次,如果跳出狹義的開戒界域,整個阿拉斯加的猶太人定居地也可以看作是一個以色列的縮影。書中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該地區同時還居住著特林吉特人,即世代居住于阿拉斯加的印第安土著,他們跟猶太移民之間的關系一直非常緊張,雙方甚至時有暴力沖突發生。事實上,這些印第安人在小說中具有隱喻的功能,代表了真實歷史中被剝奪住所的巴勒斯坦人。
猶太彌賽亞主義:無盡的延緩以上所分析的空間政治,除了暗指猶太復國主義的領土觀念與暴力傾向外,還體現出夏邦本人的宗教觀念,特別是對篤信救世主降臨的猶太彌賽亞主義(JewishMessianism)極不認同。以故事開頭的死者施皮爾曼為例,早在童年時代,此人就展現出驚人的稟賦———他能夠講多種語言,棋藝高超,而且還施過神跡,因而被很多猶太人視為潛在的彌賽亞、每一代人中只會出現一次的“柴迪克”(Tzadikha-Dor),此為猶太教的一個封號,意即“持守公義之人”。
然而頗有意味的是,這位“未來的彌賽亞”恰好出生于希伯來歷的埃波月9日,即歷史上耶路撒冷圣殿被毀的日子,這一巧合預示了他從一開始就注定走向毀滅的宿命。這種“天命”反映在他尸體旁邊那盤未下完的棋局上———蘭茲曼后來發現,余下的棋局其實是一個“迫移”(Zugzwang,也叫“楚茨文格”),即對弈一方必須出招,但無論他怎么走,都將對自己不利,最終只能一步步走向敗局。由此可見,哪怕像施皮爾曼這樣的國際象棋天才,都無力擺脫“迫移”的約束,逐步走向自己的覆滅,更遑論他人。
這一棋局,在某種程度上象征著彌賽亞降臨的不可能,人們為此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只能是徒勞。在更大范圍里,它也指向一種近乎存在主義的人生觀———從表面上看,每一步棋都代表著人的自由意志(特別是自由選擇的能力),可無論你如何落子謀局,人生總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荒誕與虛無。也就是說,所謂的“選擇權”其實只是一個幻象,但既然“存在”于這個世界上,人類又別無他法,便只能通過自己的選擇和行動,來創造自己的“本質”,于無意義之處找尋意義。
結語
由上述分析可見,夏邦對猶太空間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宗教理念極不認可———書中著力刻畫的孤島意象與開戒界域,體現了正統派猶太人的墨守成規和自欺欺人;發生在猶太人聚居點的各種權力爭斗,暗指真實的以色列國的領土政策以及猶太民族的暴力傾向;而書中的核心場景(即神秘兇案和迫移棋局)則象征了作者眼中彌賽亞降臨的不可能,并借此暗諷了現實世界中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特別是對以政策)。
當然,盡管夏邦不贊同傳統的猶太復國主義和彌賽亞主義,但讀者在書中依然能找到一些相關的正面描寫———如克拉維茨所言,故事中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從而被推上了一條向死之路……作品為這種努力賦予了一種崇高感,這本身就是對猶太人生和思想的一種肯定”(Kravitz,2010:108)。這不免讓人想起存在主義哲學家加繆(AlbertCamus,1913-1960)筆下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遭受諸神的懲罰,不斷將滾下山的巨石推向山頂,如此周而復始、永不停歇;這位荒誕的英雄明知自己的所為純屬徒勞,但依然可以從這一過程中獲取滿足和快樂,無怪乎加繆說:“向上攀爬的奮斗本身即足以填充一個人的內心。我們必須設想西西弗斯是開心的”(Brée,1972:88)。
西方文化論文范例:論西方經典劇作本土化改編的創新與不足
同樣道理,猶太復國主義者為了自己的信仰而奮斗,盡管其手段未必讓人認同,其結果也并不遂人意,但這一過程本身即是在實踐自由意志、塑造自身本質。從這個角度看,這些“西西弗斯式的英雄”依然值得人們的尊重。由是觀之,夏邦在書中對猶太復國主義和彌賽亞主義指責與敬仰并存的矛盾態度,在某種程度上也就可以理解了。
作者:李鋒
SCI論文
- 2023-07-06博士有SSCI期刊發表論文經歷重要
- 2022-11-10ssci從投稿到發表要多久?
- 2024-04-01ANNALS OF PHYSIC最新分區是幾區
SSCI論文
- 2023-06-14發ssci論文能查到嗎查詢流程
- 2023-08-24論文發表多久可以被ssci收錄
- 2023-12-25AHCI發表論文算學術成果嗎
EI論文
- 2022-12-07ei期刊論文發表有難度嗎
- 2023-06-28ieee xplore 是ei檢索嗎
- 2023-02-07ei會議提前多久開始征文
SCOPUS
- 2023-03-20scopus高級檢索功能怎么用?
- 2023-04-12scopus數據庫收錄哪些門類的文獻
- 2023-03-28scopus收錄哪些學科的期刊
翻譯潤色
- 2023-05-06基因測序文章怎么翻譯潤色
- 2023-05-09鍛造相關中文文章怎么翻譯為英文
- 2023-05-11生物醫學sci論文潤色有用嗎
期刊知識
- 2020-08-05sci論文怎么修改
- 2022-04-02論文三版起發需要寫多少字
- 2015-06-05發表宗教類文章的核心期刊
發表指導
- 2020-07-28臨床麻醉論文發表選刊方法
- 2022-03-15留守兒童教育已發表過的論文
- 2018-03-17審稿快的生物類核心期刊多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