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蘇輿對(duì)董、何“三正”說(shuō)的批評(píng)與詮釋
時(shí)間:2020年06月07日 分類(lèi):文學(xué)論文 次數(shù):
【摘要】《春秋公羊傳》通過(guò)“通三統(tǒng)”例,以“存三正”的方式處理王朝更迭后新王與舊王間的關(guān)系,用“存二王后”的形式保留前朝社稷、服色,籍此展現(xiàn)“尊先王”之意。清末學(xué)者蘇輿通過(guò)分疏兩位漢代《公羊》學(xué)先師董仲舒、何休對(duì)“以《春秋》當(dāng)新王”一旨的不同詮釋?zhuān)约?ldquo;親周”與“新周”的異文,成功地構(gòu)建了董仲舒與何休對(duì)“三統(tǒng)”詮釋的兩處矛盾,并以《春秋》“只改正朔而不易王統(tǒng)”為基點(diǎn),憑借將商、周、漢通為三統(tǒng)的理論構(gòu)建,批駁了何休以降的今文學(xué)家所認(rèn)同的《春秋》“黜周王魯”說(shuō),否定了康有為本諸“通三統(tǒng)”例而構(gòu)建的“改制”之論。但蘇輿對(duì)董仲舒“統(tǒng)三正”說(shuō)的詮釋完全建立在對(duì)何休“通三統(tǒng)”論的批駁上,帶有強(qiáng)烈的學(xué)術(shù)及政治主觀性,亦未必董氏學(xué)之本意。
【關(guān)鍵詞】蘇輿;何休;董仲舒;通三統(tǒng);三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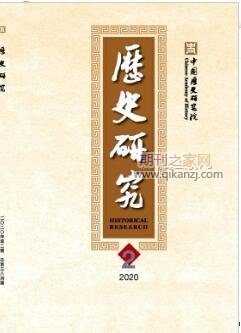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晚清今文學(xué)家著力發(fā)揮《公羊》學(xué)所蘊(yùn)含的“改制”學(xué)說(shuō),對(duì)當(dāng)時(shí)學(xué)術(shù)與政治風(fēng)氣影響巨大。與此同時(shí),以蘇輿為代表的另一派學(xué)者雖亦推崇《公羊》學(xué),但在今、古文間作持平之論,并不認(rèn)可康有為的“孔子改制”學(xué)說(shuō)。近年來(lái),蘇輿的《春秋》學(xué)也吸引了許多學(xué)者的注意。例如,李強(qiáng)指出,蘇輿《春秋》學(xué)承續(xù)孔廣森、凌曙、陳立,其大旨專(zhuān)在批駁康有為
參見(jiàn)李強(qiáng):《康有為和蘇輿〈春秋繁露〉研究之比較》,博士學(xué)位論文,湖南大學(xué)岳麓書(shū)院,2013年,第177—179頁(yè)。;姜廣輝、李有梁認(rèn)為,蘇輿試圖通過(guò)撰寫(xiě)《春秋繁露義證》,在批駁康有為“改制”說(shuō)的同時(shí),恢復(fù)董仲舒《春秋》學(xué)的本來(lái)面貌參見(jiàn)姜廣輝、李有梁:《維新與翼教的沖突和融合——康有為、蘇輿對(duì)〈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讀》,《天津社會(huì)科學(xué)》2010年第3期。。作為康有為基于“三統(tǒng)”論之“改制”學(xué)說(shuō)的堅(jiān)定反對(duì)者,蘇輿通過(guò)對(duì)“通三統(tǒng)”中“以《春秋》當(dāng)新王”一旨的貶壓,提出了一種對(duì)《公羊傳》“三正”說(shuō)的新詮釋。
一、“通三統(tǒng)”與“存三正”在《公羊》學(xué)中的淵源
蘇輿作為岳麓書(shū)院末代山長(zhǎng)王先謙的高足,曾一度被推舉為清末民初時(shí)湖南地區(qū)“翼教”運(yùn)動(dòng)的先鋒人物,無(wú)論在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還是政治傾向上,其反對(duì)康有為的態(tài)度都非常堅(jiān)決。然而,康有為雖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其核心理論卻并非臆造,而多是本于《公羊傳》。蘇輿與康有為的論爭(zhēng)核心在于:《公羊傳》中的所謂“微言大義”,除了為人所熟知的“尊王攘夷”和“誅討亂臣賊子”之外,究竟是否包含“改制”的含義?
康有為對(duì)“改制”的闡發(fā),基于《公羊》學(xué)“三科九旨”中的“通三統(tǒng)”一例。“三科九旨”義例最初為東漢經(jīng)師何休所創(chuàng)發(fā),分為“張三世”“通三統(tǒng)”“異內(nèi)外”三部分,三例各一科三旨。而“通三統(tǒng)”之一科三旨為:新周、故宋、以《春秋》當(dāng)新王。“通三統(tǒng)”的主旨在于梳理新王朝與舊王朝間的關(guān)系,并確定舊王朝之遺存在新王朝建立后的位置:
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統(tǒng)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lè),所以尊先圣,通三統(tǒng),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于是可得而觀之。[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李學(xué)勤主編“十三經(jīng)注疏標(biāo)點(diǎn)本”,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第35頁(yè)。
按照何休的解釋?zhuān)碌耐醭⒅螅⒉粦?yīng)該讓剛剛被取代的舊王朝立即向自己俯首稱臣,而應(yīng)該給予其一塊封地,不必稱臣納貢,反而保留其社稷、制度,以備參征。而具備這樣歷史地位的舊王朝在何休看來(lái)應(yīng)該有兩個(gè),即所謂“存二王后”。以周朝為例,在周建立后,應(yīng)該分封夏朝及殷商之后人為二王后,建立封地,保留歷史地位及制度,不與其它諸侯國(guó)同列。事實(shí)上,在周武王大封八百諸侯之時(shí)確實(shí)是這樣操作的,夏、殷之后分別被封在杞國(guó)和宋國(guó),爵位為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中最高的公爵。正如孔子所說(shuō):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論語(yǔ)·八佾》)
可見(jiàn),何休“三統(tǒng)”說(shuō)確實(shí)有周人存夏、殷之后于杞、宋的歷史依據(jù),故而將夏、商與周并存為“三正”,并以此為根基構(gòu)建了《春秋》中的“通三統(tǒng)”例。但“通三統(tǒng)”例最大的問(wèn)題并不是存夏、殷之后為二正,而是在何休的解釋中,周禮在春秋時(shí)已經(jīng)崩壞,周朝不再具備統(tǒng)治天下的能力。因此,應(yīng)該仿照周人取代殷商之例,將周王黜為二王之后,以《春秋》當(dāng)新王,建立新的王朝秩序。雖然這種構(gòu)建僅僅是在文辭上進(jìn)行,并不可能改變實(shí)際的歷史格局,但這種假說(shuō)帶來(lái)兩個(gè)值得討論的問(wèn)題:其一,周人存夏、商之后于杞、宋,是否就意味著只能存二王后?因?yàn)樵谥艹⒅畷r(shí),可以考見(jiàn)的前代王朝只有夏、商二者,存二王后究竟是一個(gè)“三正”的理論構(gòu)建,還是存在其它可能性?其二,如果說(shuō)“三正”說(shuō)得以確立,那如何處置被從“二王后”中逐出的先王之后?
何休對(duì)以上兩個(gè)問(wèn)題的回應(yīng)非常明確:首先,連帶二王之后與新王的存正之?dāng)?shù)為三,故而稱為“三正”。而被罷黜的二王之后,應(yīng)被降為諸侯。事實(shí)上,“通三統(tǒng)”例的構(gòu)建是在對(duì)這兩個(gè)問(wèn)題的回應(yīng)中完成的。“新周故宋”就是要以周為新的二王后,將殷人之后的宋國(guó)推為舊的二王后。在這種情形下,夏人之后的杞國(guó)就要被逐出“二王后”的序列。
《公羊傳》在魯僖公二十七年有這樣一條記載:“春,杞子來(lái)朝。”同上,第254頁(yè)。杞國(guó)為夏人之后,其爵位為公爵,但在此條記載中,杞公卻被稱為“杞子”,被貶稱為子爵。雖然《公羊傳》對(duì)杞公貶稱子爵的解釋是因?yàn)槠?ldquo;無(wú)禮不備”,但何休認(rèn)為“《春秋》欲新周故宋,而黜之稱伯”同上,第254頁(yè)。。在他看來(lái),此處杞公貶稱杞子的主要原因在于,《春秋》要將杞從“二王后”中罷黜。因此,其爵位從公爵降二等為伯爵,又因其無(wú)禮再貶稱一等,故以子爵稱之。
雖然“通三統(tǒng)”例為何休所確立,但無(wú)論是“三正”說(shuō)的提出,還是“以《春秋》當(dāng)新王”的闡釋?zhuān)贾辽僭谖鳚h時(shí)便已形成雛形。尤其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zhì)文》篇中,已有以“三正”為基準(zhǔn)的、對(duì)如何處置過(guò)往王朝后裔的論述:“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fù)者,有三而復(fù)者,有四而復(fù)者,有五而復(fù)者,有九而復(fù)者。”[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7年,第200—201頁(yè)。包括“三統(tǒng)遞用”原則在內(nèi),董仲舒對(duì)過(guò)往王朝共羅列“不易”“再?gòu)?fù)”“三復(fù)”“四復(fù)”“五復(fù)”“九復(fù)”六種情形。
由于今本《春秋繁露》存在大量文本脫漏、訛誤,對(duì)于如何解釋董仲舒所列的這六種情形并無(wú)定說(shuō)。但按照蘇輿對(duì)今本《三代改制質(zhì)文》的注解,對(duì)此六者的詮釋全部圍繞“三統(tǒng)”而展開(kāi):所謂“不易”者指的是“王者必受命而后王”;“再而復(fù)”者指的是文和質(zhì);自“三而復(fù)”者起,便開(kāi)始代指正朔,所謂“三復(fù)”也就是“三正”之意,即今王與二王之后通為三統(tǒng),“正朔三而改,文質(zhì)再而復(fù)”[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201頁(yè)。;而二代之前的五位王者被列為“五帝”;“五帝”之前則為“九皇”。無(wú)論“三復(fù)”“五復(fù)”“九復(fù)”,都是針對(duì)過(guò)往王朝而言。
此外,以“三正”為核心的先朝安置體系,在董仲舒的論述中也已成型:“三代改正,必以三統(tǒng)天下。”同上,第195頁(yè)。董仲舒不但強(qiáng)調(diào)“存二王后”是“三統(tǒng)”之核心,還論述“正”與“統(tǒng)”的關(guān)系:“其謂統(tǒng)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tǒng)致其氣,萬(wàn)物皆應(yīng),而正統(tǒng)正,其余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同上,第197頁(yè)。也就是說(shuō),“正”是“統(tǒng)”的先決條件,如果沒(méi)有正統(tǒng)的歷史地位,那么便不具備統(tǒng)治天下的資格。筆者認(rèn)為,何休“通三統(tǒng)”中“新周,故宋,以《春秋》當(dāng)新王”之意亦源自董仲舒,董氏非常明確地指出其“統(tǒng)三正”說(shuō)中“絀夏”之意:“絀夏,存周,以《春秋》當(dāng)新王。”同上,第200頁(yè)。在董仲舒之后,班固在《白虎通》中專(zhuān)門(mén)撰述《三正篇》,就“三統(tǒng)”之意做理路闡發(fā):“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tǒng),謂三微之月也。”[清]陳立撰、吳則虞點(diǎn)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shū)局,1994年,第362頁(yè)。(中華書(shū)局本標(biāo)點(diǎn)為:“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tǒng),謂三微之月也。”)
可見(jiàn),“三正”說(shuō)在董仲舒時(shí)便已形成,而“三統(tǒng)”說(shuō)則在董仲舒提出“統(tǒng)三正”的基礎(chǔ)上,經(jīng)過(guò)班固等人的詮釋?zhuān)罱K由何休對(duì)之加以刪減、完善,在《春秋公羊經(jīng)傳解詁》中確立。可以說(shuō),無(wú)論在董仲舒還是何休的《公羊》學(xué)理論中,“三正”及“三統(tǒng)”都是核心內(nèi)容。對(duì)此,蘇輿也無(wú)法否認(rèn):“古王者改制,有三復(fù)、五復(fù)、四復(fù)之不同。董所主則以三統(tǒng)為說(shuō)。”[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86頁(yè)。既然董、何對(duì)“三統(tǒng)”說(shuō)都尤為重視,而“三統(tǒng)”說(shuō)的核心意義又在于罷黜杞國(guó)的“二王后”地位,以周、宋作為新的二王后,那“以《春秋》當(dāng)新王”的“改制”意味便無(wú)法否定。康有為的“改制”學(xué)說(shuō),亦基于董、何對(duì)“三統(tǒng)”說(shuō)中改元立新王之意的解釋。既然如此,蘇輿又如何能夠否定“三統(tǒng)”中的“改制”意義呢?
二、《春秋》是否為新王?蘇輿對(duì)何休“三正”說(shuō)的批評(píng)
《公羊》學(xué)對(duì)中國(guó)經(jīng)學(xué)的影響,殆不可能脫開(kāi)“三科九旨”而言。也就是說(shuō),如果蘇輿只批評(píng)康有為而不批評(píng)董仲舒、何休,那么其批評(píng)也無(wú)法觸及康氏“改制”說(shuō)的核心。反之,蘇輿對(duì)康有為的批判便需要冒著否定整個(gè)《春秋》學(xué)傳統(tǒng)的風(fēng)險(xiǎn)。事實(shí)上,蘇輿非但無(wú)意質(zhì)疑《公羊傳》,反而對(duì)董仲舒的《春秋》學(xué)青睞有加。面對(duì)這一矛盾,蘇輿選擇通過(guò)對(duì)“三正”與“三統(tǒng)”另作詮釋?zhuān)瑏?lái)否定其“改制”意味。
然而,無(wú)論是董仲舒的“絀夏,存周,以《春秋》當(dāng)新王”,還是何休的“新周,故宋,以《春秋》當(dāng)新王”,無(wú)不強(qiáng)調(diào)“黜周王魯”的寓意。雖然以《春秋》當(dāng)新王只存在于文辭上,但卻是“三統(tǒng)”說(shuō)得以建立的關(guān)鍵,必然涉及到改正朔、易服色的改制問(wèn)題。蘇輿對(duì)這一問(wèn)題的處理,建立在區(qū)分董、何的基礎(chǔ)上。在他看來(lái),雖然董仲舒、何休都提及“三統(tǒng)”,但董仲舒并未明確表示“統(tǒng)三正”說(shuō)與《春秋》間的聯(lián)系,而何休則將之列為《公羊傳》的“三科九旨”之一。也就是說(shuō),“三正”說(shuō)可以作為一個(gè)政治理論存在,也可以只是一個(gè)歷史事實(shí),未必與《春秋》詮釋完全貼合。何休“三科九旨”中的“三統(tǒng)”一義,并不需要與《春秋》大義有必然聯(lián)系:“至以《春秋》當(dāng)新王諸義,不見(jiàn)于《傳》,蓋為改正而設(shè),與《春秋》義不必相屬。”[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84頁(yè)。如此一來(lái),蘇輿將矛頭同時(shí)對(duì)準(zhǔn)康有為和何休,否定“通三統(tǒng)”說(shuō)在《公羊傳》詮釋中的指導(dǎo)地位,從根本意義上降低了“以《春秋》當(dāng)新王”說(shuō)對(duì)《公羊傳》文本闡發(fā)的影響。
不難看出,蘇輿的做法其實(shí)是奉董仲舒為正宗,借著對(duì)董仲舒《春秋》學(xué)的闡發(fā),否定何休及晚清公羊家的“三統(tǒng)”及“改制”諸說(shuō)。然而,“三統(tǒng)”說(shuō)并非何休的創(chuàng)造,“以《春秋》當(dāng)新王”甚至就是董仲舒率先提出的。如果要否定“三統(tǒng)”說(shuō),那么僅靠“以董批何”的立場(chǎng)顯然是不夠的。事實(shí)上,蘇輿對(duì)于“三統(tǒng)”說(shuō)的不滿集中在“以《春秋》當(dāng)新王”一旨,而并非“通三統(tǒng)”整例,但由于何休的“通三統(tǒng)”說(shuō)以“黜周王魯”為核心,其詮釋會(huì)不可避免地導(dǎo)向“改制”。因此,蘇輿必須解構(gòu)“三統(tǒng)”與“以《春秋》當(dāng)新王”間的必然聯(lián)系。為此,蘇輿著力強(qiáng)調(diào)班固對(duì)“三統(tǒng)”所作的“本天有三統(tǒng),謂三微之月也”解釋的合理性:“取三微之月,各法其一,以為正色。”同上,第185頁(yè)。
班固對(duì)“三統(tǒng)”說(shuō)的解釋非常平實(shí),僅強(qiáng)調(diào)王者“尊先王”的意涵:“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后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tǒng)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jǐn)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lè),永事先祖。”[清]陳立撰、吳則虞點(diǎn)校:《白虎通疏證》,第366頁(yè)。而這一論述非常符合蘇輿對(duì)“三正”的理解。在他看來(lái),“三正”最主要的含義只在于存二王后,除了尊先王和保留宗廟社稷外,完全沒(méi)有所謂“以《春秋》當(dāng)新王”的改制意涵。可見(jiàn),蘇輿其實(shí)非常認(rèn)可“存三正以通三統(tǒng)”的重要性,他批評(píng)何休及晚清公羊家所倡“通三統(tǒng)”例是“為何注所誤,讀董子未明”[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90頁(yè)。,其主要著力點(diǎn)不在于“存三正”的制度,而主要在于駁斥“以《春秋》當(dāng)新王”說(shuō)。
前文已述,“以《春秋》當(dāng)新王”明見(jiàn)于《春秋繁露》原文,蘇輿自不能視而不見(jiàn)。但他敏銳發(fā)現(xiàn)了董仲舒、何休對(duì)“以《春秋》當(dāng)新王”解釋的微妙區(qū)別:“以《春秋》當(dāng)新王”的“改制”意涵,一定要放在“通三統(tǒng)”的一科三旨內(nèi)才能得到完全發(fā)揮。蘇輿所做的恰恰是否定“以《春秋》當(dāng)新王”作為一旨的理論地位。《春秋繁露》對(duì)“王正月”的解釋是:
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lè),一統(tǒng)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yīng)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同上,第185頁(yè)。
新王受命,雖然勢(shì)必要改正朔、易服色,但“三統(tǒng)”之意即止于此,只在安置新舊王者間的關(guān)系,而絕無(wú)革命立新王的“黜周”含義。所以,只能將“三統(tǒng)”視作對(duì)歷史事實(shí)的解釋?zhuān)豢梢詫⒅鳛榻?jīng)學(xué)中的政治操作原則看待。
今文學(xué)家對(duì)“以《春秋》當(dāng)新王”的詮釋確實(shí)與“黜周王魯”緊密結(jié)合。劉逢祿云:“王魯者,則所謂以《春秋》當(dāng)新王也。”[清]劉逢祿撰、曾亦點(diǎn)校:《春秋公羊經(jīng)何氏釋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2頁(yè)。段熙仲曰:“先儒多言孔子作《春秋》以當(dāng)一王之法,所謂以俟后圣也……此一王之法或曰孔子素王,或曰為漢制,或曰王魯。”[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qū)W講疏》,南京: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第470頁(yè)。
在這個(gè)意義上,“新王”并不一定是《春秋》、魯或者漢,其實(shí)質(zhì)是如包慎言所說(shuō)的“因魯以明王法”[清]陳立撰、劉尚慈點(diǎn)校:《公羊義疏》,北京:中華書(shū)局,2017年,第16頁(yè)。。然而,蘇輿籍此成功構(gòu)建了董仲舒與何休以降的今文學(xué)家間的矛盾:董仲舒的“三統(tǒng)”說(shuō)是對(duì)歷史事實(shí)的解釋?zhuān)涡荨⒖涤袨榈葎t要借“以《春秋》當(dāng)新王”表達(dá)“改制”的政治意圖,甚至加以實(shí)踐。
這種對(duì)何休以降今文學(xué)家的質(zhì)疑也不是晚清才產(chǎn)生的。徐彥就曾對(duì)“以魯隱公為受命王,黜周為二王后”一說(shuō)的質(zhì)疑作了答復(fù):“隱公之爵不進(jìn)稱王,周王之號(hào)不退。”[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第3頁(yè)。也就是說(shuō),“黜周王魯”并非真的以魯隱公為受命王,而只是“托王”,事實(shí)上仍然以周王為天下共主。然而蘇輿并不這樣認(rèn)為,在他看來(lái),即便只是借之以明王法,“黜周王魯”也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說(shuō)僅僅把“以《春秋》當(dāng)新王”視作改正朔,否認(rèn)“黜周王魯”的解說(shuō),那么《春秋》為漢立法的意義就被消解了,漢代《公羊》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都將受到質(zhì)疑。事實(shí)上,蘇輿不可能全盤(pán)否定《公羊》學(xué),他繞過(guò)“以《春秋》當(dāng)新王”與“黜周王魯”,將“尊周”與“尊漢”直接聯(lián)通,在一定程度上給了這一問(wèn)題一個(gè)較為合理的詮釋。
雖然漢代今文經(jīng)學(xué)家都聲言《春秋》為漢制作,然而無(wú)論是在三統(tǒng)遞進(jìn)還是五行生克的理論中,漢儒對(duì)于漢代的定位都并不明確,無(wú)論是尚黑、尚白還是尚赤,在不同文獻(xiàn)中都能找到依據(jù)。從這個(gè)層面上說(shuō),質(zhì)疑《春秋》為漢制作也不無(wú)道理。然而,按照段熙仲的解釋?zhuān)?ldquo;為漢制作”和“王魯”其實(shí)都是在講同樣的“一王之法”,那么為什么到了漢儒的理解中就有這么多的歧義呢?
其實(shí),從漢以降諸儒對(duì)于秦朝在三統(tǒng)及五行學(xué)說(shuō)中的定位,或許更能理解蘇輿的詮釋。自漢以降,儒者們大多不認(rèn)可秦朝具備正統(tǒng)地位。蘇輿在《義證》中也引用《史記》《漢書(shū)》及許多東漢時(shí)期的讖緯文獻(xiàn),證明漢人以秦朝暴虐為由,不以之為受命王。其中,兩條材料值得注意:一是引述晉代黜秦的做法:“晉尊二王之后,只及周、漢,不數(shù)秦,正用漢儒義。”[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88頁(yè)。二是引用朱一新的觀點(diǎn):“蓋漢承秦統(tǒng),學(xué)者恥言,故奪黑統(tǒng)歸《春秋》。”同上,第187—188頁(yè)。
此說(shuō)雖出朱一新,但從蘇輿的表達(dá)來(lái)看,他對(duì)秦代是否為一統(tǒng)的看法似乎與前人又有不同。如前所言,秦?zé)o論是在五德輪回說(shuō)中屬水德,還是在三統(tǒng)理論中尚黑,在各種漢代文獻(xiàn)的記載中是基本一致的,并無(wú)太大爭(zhēng)議。反而是漢代究竟是否為火德,其統(tǒng)紀(jì)為白統(tǒng)、赤統(tǒng)還是黑統(tǒng),歷來(lái)有著不同說(shuō)法。也就是說(shuō),無(wú)論漢初學(xué)者是否認(rèn)可秦正統(tǒng),秦在歷史事實(shí)上的一統(tǒng)是不能否認(rèn)的。很明顯,當(dāng)時(shí)的學(xué)者早已在三統(tǒng)與五德兩種理論中為其找到了位置。但漢代建立之后,因?yàn)榍氐谋┡岸阉懦獾秸y(tǒng)之外,卻要面臨秦在五德及三統(tǒng)中都已經(jīng)有位置的實(shí)際情況。
不同的學(xué)者就選擇了不同的做法:其一是直接忽略秦,將漢視為黑統(tǒng)。但是漢尚黑統(tǒng)說(shuō)在歷史上被引述最少,蘇輿也引證司馬遷的說(shuō)法,認(rèn)為此說(shuō)在當(dāng)時(shí)的認(rèn)可度最低。其二則是漢尚赤說(shuō)。此說(shuō)雖廣被引用,但尚赤與赤統(tǒng)又有不同,尚赤說(shuō)的理論根據(jù)是認(rèn)為漢為堯后,而漢為赤統(tǒng)又屬五德輪回說(shuō)中的理論,并不屬于三統(tǒng)理論。蘇輿認(rèn)為,漢承堯后而尚赤之說(shuō)屬于古文經(jīng)學(xué)的說(shuō)法,要晚于董仲舒:“在董子時(shí),尚無(wú)此說(shuō),故取赤統(tǒng)不始唐堯。”同上,第187頁(yè)。所以,董仲舒以《春秋》一統(tǒng)代替秦,是最為后世所接受的說(shuō)法,最大程度避免了秦在實(shí)際上為一統(tǒng)、而在《春秋》學(xué)中又不能占據(jù)一統(tǒng)的矛盾。
按照這一原理推論,那么漢代自然應(yīng)該尚白統(tǒng)無(wú)疑。蘇輿認(rèn)可這種論斷。在他看來(lái),所謂“以《春秋》當(dāng)新王”,正是在揚(yáng)漢抑秦的原則下,解說(shuō)《春秋》的假設(shè):“尊《春秋》即所以尊漢也。”同上,第188頁(yè)。蘇輿雖然清楚認(rèn)識(shí)到這一條例的內(nèi)在理路,但仍舊不能認(rèn)可“通三統(tǒng)”例中“以《春秋》當(dāng)新王”的解釋。他試圖用另一種方式解決這一問(wèn)題,即完全否認(rèn)秦的地位,直接將殷、周、漢通為三通。在這種意義上,“以《春秋》當(dāng)新王”便只意味著改正朔。也就是說(shuō),雖然孔子作《春秋》為后世法,但王者仍然為周不變,真正的改易王者要等到漢代。蘇輿所引述的晉代存二王后的做法,也是將殷、周、漢通為三統(tǒng)的歷史依據(jù)。
三、“新周”與“親周”:蘇輿對(duì)“三正”詮釋的局限
除“以《春秋》當(dāng)新王”外,蘇輿對(duì)何休“通三統(tǒng)”例的批評(píng)還關(guān)注了“新周”一旨。“新周”之要義在于黜周為二王后,而蘇輿自然要對(duì)涉及改制作新王的“黜周”說(shuō)予以堅(jiān)決貶斥。從這個(gè)角度說(shuō),其對(duì)“新周”說(shuō)予以批判并無(wú)不當(dāng)。由于蘇輿基于對(duì)“以《春秋》當(dāng)新王”的解釋構(gòu)建了董仲舒與何休之間的矛盾,“新周”說(shuō)是可以在其建構(gòu)的正朔改立體系中解釋通順的。所以,蘇輿對(duì)“新周”說(shuō)的批評(píng)并不在“黜周”論的延伸,而是基于《春秋繁露》與《春秋公羊經(jīng)傳解詁》的異文,構(gòu)建了董、何對(duì)“三統(tǒng)”詮釋的第二重矛盾。
這第二重矛盾的核心在于,何休“三科九旨”中的“新周”,在董仲舒《三代改制質(zhì)文》中記作“親周”或“存周”,并無(wú)“新周”之文。首先,何休“新周”說(shuō)在其“通三統(tǒng)”例中的闡釋?zhuān)瑹o(wú)論是前后文的對(duì)照,還是上下文旨意的呼應(yīng),都不存在任何問(wèn)題,因而“新周”文本并不存在訛誤。清代學(xué)者盧文弨校對(duì)《三代改制質(zhì)文》,據(jù)上下文中“親夏”“親赤統(tǒng)”“親黑統(tǒng)”等語(yǔ)俱作“親”而非“新”,推論《春秋繁露》中的“親周”也非錯(cuò)文,而是董仲舒之原意[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89頁(yè)。。如此,何休“新周”與董仲舒“親周”的第二重矛盾,又被蘇輿構(gòu)建出來(lái)。
相比于何休“新周”說(shuō)之主旨在黜周為二王后,對(duì)董仲舒“親周”說(shuō)的理解有更多詮釋空間。蘇輿便列舉了兩種不同的觀點(diǎn):一是司馬遷的詮釋?zhuān)鳛槠湮谋疽罁?jù)的“據(jù)魯親周故宋”雖然較之何休只有“親”和“新”的差別,但其意義有明顯改變:“據(jù)魯于周則親,于宋則故。”同上,第190頁(yè)。司馬遷的這種解釋可做很多層意義的詮釋?zhuān)阂环矫妫攪?guó)為周公之子伯禽封地,屬周王室宗親,無(wú)論血緣關(guān)系還是政治聯(lián)系,魯國(guó)與周王室的關(guān)系都比宋國(guó)更為親近;另一方面,“親”與“故”的上下文呼應(yīng),又并不能否認(rèn)其時(shí)間上的新、舊含義。
二是司馬貞《史記索隱》的解釋?zhuān)?ldquo;時(shí)周雖微,而親周者,以見(jiàn)天下之有宗主也。”同上,第190頁(yè)。親周,《史記索隱》作“親周王”。([漢]司馬遷撰、[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jié)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8年,第1943頁(yè)。)這一說(shuō)法與何休截然相反,非但否定“新周”中的“黜周”意味,反而將周王室仍為天下宗主的意義凸顯出來(lái)。司馬貞的論點(diǎn)顯然更貼合于蘇輿的意見(jiàn),他依據(jù)司馬遷和司馬貞的這兩種解釋批評(píng)了何休:“劭公昧于董,兼盲于史,既動(dòng)引此文以釋經(jīng)傳,又因王魯造為黜周之說(shuō)。”[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90頁(yè)。然而蘇輿自己也清楚,司馬貞的解釋實(shí)在是與董仲舒“應(yīng)天作新王”之義太不貼合,故而,蘇輿只能更多依靠對(duì)司馬遷之說(shuō)的解釋來(lái)對(duì)抗何休。
蘇輿對(duì)“親周”的詮釋也借鑒了“張三世”例的表達(dá)方式:“史公學(xué)于董生,故其說(shuō)頗與之合。蓋差世遠(yuǎn)近以為親疏,推制禮以明作經(jīng)之旨,理自可通。由一代言之,則有所聞、所見(jiàn)、傳聞之不同,由異代言之,則有本代、前代之不同,其歸一也。”同上,第189—190頁(yè)。蘇輿不但藉此否定何休,更接連批了孔廣森、劉逢祿、康有為等清代公羊?qū)W家。然而,其理由仍然只停留在他們遵從于何休的“新周”而忽視董仲舒的“親周”。筆者認(rèn)為,何休與董仲舒的這種矛盾很大程度上是蘇輿刻意構(gòu)建出來(lái)的,《春秋繁露》本便明言“以《春秋》當(dāng)新王”,“新周”一旨的所有含義都本之于《三代改制質(zhì)文》,在義理上與董仲舒并無(wú)顯著矛盾。
蘇輿對(duì)董仲舒“親周”說(shuō)的詮釋?zhuān)Y(jié)合其通殷、周、漢為三統(tǒng)的“三正”說(shuō),否定了何休“三正”說(shuō)中的《春秋》為新王論。但其不易姓而只改正朔的理論,事實(shí)上只是對(duì)漢代黜秦理論的一種可能性詮釋?zhuān)茈y對(duì)《春秋》中的“三統(tǒng)”論做出實(shí)質(zhì)性改變。而且,蘇輿對(duì)董仲舒的詮釋還存在另一個(gè)巨大的問(wèn)題:在《三代改制質(zhì)文》中,除“親周故宋”外,還有“親夏故虞”和“親殷故夏”的說(shuō)法,這兩者不但可以證明“黜周王魯”的理路仍舊可以貫通于《三代改制質(zhì)文》,而且非常不利于蘇輿“據(jù)魯于周則親”的解釋。從這點(diǎn)上說(shuō),盧文弨的校勘其實(shí)更能支持何休而不是蘇輿的解釋。也就是說(shuō),董仲舒的“三統(tǒng)”說(shuō)并無(wú)法通過(guò)“親”與“新”的異文體現(xiàn)出與何休的差異。
可見(jiàn),蘇輿以“親周”與“新周”的差別所構(gòu)建的董、何異義,事實(shí)上在對(duì)董仲舒“三正”說(shuō)的詮釋中很難成立。而其對(duì)“以《春秋》當(dāng)新王”所作的只改正朔而不改王命,留待漢王朝再接續(xù)周統(tǒng)的理論設(shè)計(jì),雖可成一家之言,但未必為董仲舒的本意。《三代改制質(zhì)文》中有“《春秋》應(yīng)天作新王之事,時(shí)正黑統(tǒng)”[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87頁(yè)。的說(shuō)法,而按照蘇輿的詮釋?zhuān)茈y將之解釋通順。首先,王者受命于天,然后改正朔。如果說(shuō)殷尚白統(tǒng)、周尚赤統(tǒng)不存在疑問(wèn),那么接續(xù)周者自應(yīng)尚黑統(tǒng)。無(wú)論是認(rèn)秦為黑統(tǒng)還是以《春秋》當(dāng)新王,都是尚黑,但蘇輿自己也認(rèn)為漢代應(yīng)該尚白而不是黑統(tǒng)。如此,便破壞了“三正”的遞用關(guān)系。
蘇輿只強(qiáng)調(diào)“以《春秋》當(dāng)新王”的改正朔意義,但既然否認(rèn)其受天命而為新王,那么非王者又何可改制?蘇輿并沒(méi)能對(duì)這個(gè)問(wèn)題給出一個(gè)合理的答復(fù)。其次,蘇輿認(rèn)為董仲舒后輩眭弘等人所持漢承堯后而尚赤之說(shuō)要晚于董仲舒,這一說(shuō)法也僅屬推測(cè),缺乏足夠的證據(jù)支持。雖然蘇輿對(duì)“五德尚赤”與“三統(tǒng)尚赤”所作的區(qū)分非常準(zhǔn)確,但他忽略了另一個(gè)問(wèn)題:如果按照《春秋繁露》給定的神農(nóng)、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夏、商、周、春秋再到漢的更替順序,漢恰是與堯共為白統(tǒng),也就是說(shuō),眭弘的觀點(diǎn)符合《三代改制質(zhì)文》中所排列的體系的順序,并不悖于董仲舒。可見(jiàn),蘇輿所秉持的殷、周、漢通為三統(tǒng)的“三正”詮釋可為一家之言,但并非唯一正確的理解。
綜上所述,蘇輿通過(guò)對(duì)“三正”說(shuō)中“以《春秋》當(dāng)新王”的詮釋與“親周”“新周”的異文,構(gòu)建了董仲舒與何休學(xué)說(shuō)間的兩處矛盾,并通過(guò)闡述對(duì)董仲舒“三正”說(shuō)的理解,否定何休“通三統(tǒng)”說(shuō)的“改制”意味。但蘇輿對(duì)董仲舒“三正”說(shuō)的解釋目的,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duì)康有為的批判上,難免帶有其強(qiáng)烈的主觀性。雖然蘇輿強(qiáng)調(diào)其對(duì)“三正”說(shuō)的詮釋在于恢復(fù)董仲舒《春秋》學(xué)的原貌,但事實(shí)上,蘇輿“只改正朔而不易王統(tǒng)”的解釋邏輯,大大壓縮了對(duì)董子“三正說(shuō)”的詮釋空間,未必是董氏學(xué)之本旨。
作者簡(jiǎn)介:陳峴,山東淄博人
歷史論文投稿刊物:《歷史研究》雜志 期刊投稿 核心發(fā)表, 雜志是歷史專(zhuān)業(yè)學(xué)術(shù)性刊物。1954年北京創(chuàng)刊,主要刊登我國(guó)史學(xué)界研究成果,內(nèi)容涉及中國(guó)古代史、近代史、現(xiàn)代史及世界史等方面的研究,刊登史學(xué)研究評(píng)介,報(bào)道史學(xué)研究動(dòng)態(tài)。
專(zhuān)項(xiàng)學(xué)術(shù)專(zhuān)題
SCI期刊目錄
熱門(mén)核心期刊目錄
SCI論文
- 2023-07-06博士有SSCI期刊發(fā)表論文經(jīng)歷重要
- 2022-11-10ssci從投稿到發(fā)表要多久?
- 2024-04-01ANNALS OF PHYSIC最新分區(qū)是幾區(qū)
SSCI論文
- 2023-12-25AHCI發(fā)表論文算學(xué)術(shù)成果嗎
- 2023-08-24論文發(fā)表多久可以被ssci收錄
- 2023-06-14發(fā)ssci論文能查到嗎查詢流程
EI論文
- 2022-12-07ei期刊論文發(fā)表有難度嗎
- 2023-02-07ei會(huì)議提前多久開(kāi)始征文
- 2023-06-28ieee xplore 是ei檢索嗎
SCOPUS
- 2023-03-28scopus收錄哪些學(xué)科的期刊
- 2023-03-20scopus高級(jí)檢索功能怎么用?
- 2023-04-12scopus數(shù)據(jù)庫(kù)收錄哪些門(mén)類(lèi)的文獻(xiàn)
翻譯潤(rùn)色
- 2023-05-06基因測(cè)序文章怎么翻譯潤(rùn)色
- 2023-05-09鍛造相關(guān)中文文章怎么翻譯為英文
- 2023-05-11生物醫(yī)學(xué)sci論文潤(rùn)色有用嗎
期刊知識(shí)
- 2022-04-02論文三版起發(fā)需要寫(xiě)多少字
- 2015-06-05發(fā)表宗教類(lèi)文章的核心期刊
- 2020-08-05sci論文怎么修改
發(fā)表指導(dǎo)
- 2022-03-15留守兒童教育已發(fā)表過(guò)的論文
- 2020-07-28臨床麻醉論文發(fā)表選刊方法
- 2018-03-17審稿快的生物類(lèi)核心期刊多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