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貴州虎患及人類社會應對
時間:2020年04月03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本文通過對地方志中有關虎的歷史記錄進行分析,對明代貴州地區虎患的烈度、時空分布、社會應對進行全方位梳理和復原。歷史文獻記載表明,隨著區域開發活動的不斷展開與深入,明代貴州地區的虎患現象在早期較少且烈度低,至中后期爆發頻繁且愈益酷烈,以正統、嘉靖、萬歷年間為主,其中嘉靖年間最為頻繁,平均每四年爆發一次。通過運用GIS手段,將虎患記錄的頻次及其區域分布可視化,發現虎患的多發區域集中在丘陵山地和盆地的東部、中部地區。針對虎患發生的不同時間、地點、烈度及受害人,其社會應對以民間、官方和僧道三個群體為主,應對方式則主要有祈禱、捕殺、感化三種。
關鍵詞:明代貴州虎患社會應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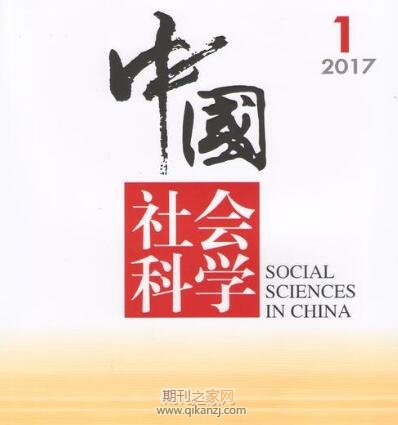
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的漫長歷史時期,作為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基本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就一直是人類文化中最原初、最基本的問題之一。毋庸諱言,人類的生存和生活必然要與自然環境發生關系,人與自然的沖突也是不可避免的。近代工業文明以來的環境問題引發了人們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重新思考,環境史學應運而生。客觀審視歷史時期的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系可為當前的人與自然永久和諧提供經驗借鑒。本文以典型動物為媒介,探討特定時期特定區域的人與動物關系。
一、研究主題說明
虎,食肉目貓科大型動物,位于食物鏈的頂端,起源于中國,[1]與人類社會在文化、生產、生活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系。自古至今,人虎之間經歷了“人崇虎-人崇虎與人虎互傷-人護虎”的關系演變。然而,其中最激烈的人虎關系則是人虎互傷,且持續時間最長、對虎種群的影響最大,其表現形式即虎患及人類社會的應對。復原歷史時期的虎患及社會應對是弄清歷史時期人虎關系特定史實的一個重要課題。
作為國家首批生態文明示范區省份之一的貴州,[2]位于云貴高原,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說,92.5%的面積為山地和丘陵。境內山脈眾多,山高谷深,茂林修竹,是歷史上野生華南虎生存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也是當前專家推測最有可能發現野生華南虎的地區之一。早在24萬年前貴州就有人類活動的蹤影,但是由于人口分布較少,且多崇山峻嶺,直到明以前幾乎沒有大規模的開發。直到明永樂十一年(1413)設置貴州承宣布政使,正式建制為省,逐漸興起了貴州開發的高潮。正是此時,開啟了人虎沖突的大幕。所謂“虎患”,是由于人類開發活動大規模侵入虎的生活領域或破壞其棲息環境,從而引發頻繁的虎對人畜的侵擾性、攻擊性事件,是人虎之間的正面沖突愈演愈烈的特有現象。
虎患是人與虎的關系史中表現最為突出、形式最激烈、對虎種群影響最大、后效最明顯的一種表現形式,也是涉及生態與環境問題最多的一個方面。關于不同地域的虎患研究,學界已有所探討,主要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虎患史料的整理、鋪陳及考述研究,[3]-[11]將虎患視作一種文化現象進行分析的研究,[12],[13]環境史視野下虎患與生態環境、人類活動關系的研究。[14]-[25]關于貴州地區的研究也有學者涉及,主要是運用傳統史學研究方法以文字鋪陳,且著重于文化觀念角度的討論。[26]-[28]然而,關于虎患,除了文字復原其發生地等信息外,其爆發的時段特征、爆發頻次、對人與物造成的損害程度等,與人虎關系的緊張程度密切相關,是決定人類采用何種應對方式的重要因素,從而對虎種群的生存狀態產生不同的影響。
因此,本文通過梳理明代的虎患記錄,運用歷史文獻考證法、動物識別法、EXCEL表格與統計法,建立虎歷史數據庫,采用GIS制圖的方法,將明代貴州地區虎患記錄的時空分布和爆發頻次可視化,并分析虎患烈度,勾勒不同人群因之采取的不同應對方式。區域性的個案研究需要相對集中、翔實的歷史文獻作為基礎,興盛于明清時期的地方志內容廣博,專門記載一地的天文、地理、政治、經濟、文化、重要人、事、物等。由于編纂人員多為當地官員士紳,極易獲取地方政府的一手檔案資料等,成為特定區域面貌的真實寫照。因此,本文的研究資料主要來自臺灣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貴州》系列和江蘇古籍出版社(今鳳凰出版社的前身)、上海書店和巴蜀書社協作出版的《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系列的130部貴州地方志,以及其他地區的方志(如同治江西《臨江府志》)中有關當代行政區劃下貴州地區的明代虎記錄。本文極力搜覽亦難免掛一漏萬,敬請方家補充、指正。
二、明代貴州虎患烈度及其時空特征
如前所述,正因為方志前后相繼的特點,相同的信息、事件在前后相繼的方志中會被重復記載,這就需要對搜集到的虎記錄進行整理,剔除無效資料,合并重復資料,然后進行統計、分析。另外,還可以利用各行政級別、各歷史時期的不同方志對歷史記錄進行相互考訂。解讀所有的虎記錄,按其記述內容可分為四個大類:虎釋名、虎祥瑞、虎物產、虎紀事。其中虎紀事又包括人虎接觸、此地有虎和虎患三個方面的內容。這些記載從不同側面反應出歷史時期人虎關系的不同表現形式。貴州地區明代共有43條確切的虎記錄,其中虎患記錄28條,超過全部虎記錄的一半,由此可見明代虎患問題的凸顯。
1.明代貴州虎患的烈度及其時段特征
學界以往研究歷史時期虎患的文章,都是將虎傷人事件統稱為“虎患”,敘述其發生的地點,卻無法區別其發生的烈度。而虎患的烈度與人虎關系的緊張程度是密切相關的。為了深入分析虎患的烈度及其對人畜造成的傷害,我們將歷史文獻中的虎患記錄根據虎數量、虎患烈度(傷人畜數量、發生地域范圍、持續時長、爆發頻次)等不同指標,劃分為4個等級:I級程度最輕,一般是一只虎與人突然相遇的偶發性事件;Ⅱ級是2-3只以上的虎主動傷人(畜)在10人(只)以下的事件。Ⅲ、Ⅳ級是“群虎”“眾虎”頻繁大規模傷害人(畜)達到“噬人百余”“不可勝計”的重大、特大虎患事件。[29]通過這樣的嘗試,可以明確人虎沖突的激烈程度。將明代貴州虎患記錄按照以上標準進行烈度分級統計。統計顯示,明代貴州虎患多集中在Ⅰ、Ⅱ級,Ⅲ、Ⅳ級已有一定程度爆發。
這表明當時貴州的虎患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虎擾人和被動傷人。Ⅰ級占比42.9%,表明虎已經對人們的生活造成了困擾;Ⅱ級虎主動傷人成患,占比達到46.4%,則說明虎患烈度加大,不再是單一虎為患傷人,已經開始三五成群,主動攻擊;而虎患烈度達到Ⅲ、Ⅳ這樣的級別,已經形成重大、特大虎患,導致幾十、上百的人畜傷亡,對百姓生產、生活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如果我們將這些不同級別的虎患根據其發生的時間復原到不同的歷史階段,會有更為細致的發現。有明一代,時長276年,歷16帝,表1可見,其中11帝在位期間發生過虎患問題。虎患記錄的時間相對集中,主要在正統、嘉靖、萬歷年間。其中嘉靖年間最頻繁,45年共爆發12次,幾乎平均每四年即發生一次虎患。有的地方甚至連年發生虎患,如,“(嘉靖)二十七年秋,銅仁虎渡江,越城攫市畜。冬至府廨,又至李參將廄,斃馬三。”“二十八年冬十月,銅仁閱兵,鹿入陣中,虎入西岔路之永順營,渡江至眾思堂,入保靖營二營。”
這兩條記錄反映出銅仁在嘉靖二十七(1548)、二十八(1549)兩年連續遭受虎患的情況,既有虎“攫市畜”“斃馬三”“至府廨”的主動擾人畜事件,又有突入軍營的偶然性侵擾事件。虎患爆發頻率次之是萬歷年間,大約平均每十年爆發一次。雖然沒有嘉靖時期頻繁,但其烈度卻大為提高,5條記錄中有3條是III、IV級虎患。有的地方不僅連年發生虎患,且烈度都極高。將重大、特大虎患資料進行統計,明代重大虎患(Ⅲ、Ⅳ級)全部集中在萬歷年間,且四次虎患傷亡總人數不低于500人。對于明永樂十一年(1413)才建制為省的貴州來說,這不可謂不是嚴重的災患。這一時期爆發的虎患其傷害力度動輒以百人計,其酷烈程度可見一斑。
虎患的多寡和強弱,是人類開發持續深入、自然(氣候)變化等多方面綜合作用的結果。明早期虎患少且烈度低,嘉靖后,爆發頻繁且烈度高,反映出其在時間分布和烈度演變上的不均衡性。這既與明代成立行省后移民大量涌入貴州,中后期加大開發導致人虎爭地有一定關系,也與貴州文獻記錄在明代興起有一定的相關性。人們對貴州山地的開發,逐漸造成人虎生活區域的重疊。人虎接觸逐漸增多,人類的開墾活動破壞了植被覆蓋,影響虎及其他動物的生存,從而引發大量虎進城覓食、侵擾和攻擊人畜的事件。開發越深入,地域越擴展,人類與虎相遇的幾率越大,對虎生存造成的擾動越大,虎患發生的頻率及酷烈程度也就隨之增加和提高。以每次虎患出現的虎數量、人畜傷亡數量,以及虎患發生時間的集中程度來看,明代中后期虎患出現的頻次已經不是一個偶然的狀況。
2.明代貴州虎患爆發的地域特征
貴州是歷史上野生華南虎生存的主要分布區之一,在貴州桐梓[30],[31]柴山崗和馬鞍山、盤縣十里坪村、[32]普定縣白巖腳洞、[33]畢節市扁扁洞、[34]興義縣張口洞遺址[35]等考古發掘中,都發現虎的骨骼或牙齒化石。這足以證明史前貴州境內就廣泛活動著華南虎,是古人類的重要狩獵對象。歷史時期分布更為廣泛。貴州民間稱老虎為“老貓”、“大貓”,甚至簡稱為“貓”,各地都有稱為“貓沖”、“老貓井”、“貓貓山”、“貓跳河”之類的地方,就是當年老虎出沒之地。今天貴陽市中心的黔靈山在歷史時期也曾有老虎出沒,九曲徑石壁上的“虎”字,就是明清時期留下的信號。
三、明代貴州虎患的社會應對
虎患的發生給人類生命、財產安全帶來了影響,根據虎患發生的時間、地點、烈度及受害人的不同,不同的人群做出了不同的應對方式。將現有全部虎記錄中含有應對信息的記錄22條進行統計分析,可得表4:一般說來,偶然性人虎相遇導致虎傷人的事件發生時,一般由直接受害人及其親屬或身邊的人做出反應,我們將這一群體歸結為“民間”應對。在明代,貴州地區的虎患有近三分之一是由這一群體做出應對的。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來自老虎的威脅時,本能的應對方式便是捕殺。如嘉靖《思南府志》載“嘉靖四年,忽一夕有虎至郡治堂吼嘯數聲而出,不知所之。又一日,三虎渡河止于通濟橋下,眾搏之而斃。”[41]再如萬歷《黔記》載“申祐,字天錫,婺川縣人,常從其父之田,道逢虎,父入虎口,公挺身持杖尾擊之,虎逸,父得免。”[42]另一方面,由于認識水平與民間信仰所限,人們有時候還會將希望寄托于神靈,通過感化老虎或祭祀祈禱來消除虎患。如,光緒《普安直隸廳志》講述了明人邵元吉帶著父親靈柩匍匐扶櫬,經播州(今遵義)遇虎,因其泣下不忍離其父柩,后虎竟被感化而未傷人離開的故事。[43]
另有,明人鄭逢元隱居茂龍塘(位于今岑鞏縣境內)時遇到虎“大出為患”,攫食公家牛豕和他準備為母親祭祀而供奉的黑羊,其采取的措施就是撰寫祈禱之文“詰責土神,言甚痛切”而消除虎患。[44]較為嚴重的虎患往往被視為地方官員為政不廉、行政不力的災異現象,因此,當虎患波及的區域較大、人畜損失加劇時,官府就會出面解決,有時甚至出動軍隊。貴州明代的虎患爆發頻繁,官府因此出面應對的次數很多,超過民間。其主要方式為撰驅虎文祈禱驅虎,同時輔以捕殺措施。如乾隆《貴州通志》卷之二十記載:“成化三年(1467),(劉宇)以貴州巡按御史降施秉縣典史,適虎為民患,宇牒城隍。明日,兩虎相噬死,患遂息。”[45]講述了作為地方官員的劉宇被貶到施秉之后,發現該地虎患嚴重,遂到城隍廟祭拜神明平息虎患的事跡。又如,同治年間的江西《臨江府志》載嘉靖年間“平灞威清諸處多虎患,(張緒)為文禱于廟,俄虎自相搏噬死。”
講述了江西人張緒在貴州做官時,作文祈于廟驅虎的事跡。道光《貴陽府志》載“貴州山多虎,出道旁伺人,信(蔣信)為文驅之,患稍息”,[46]講述了蔣信在貴州做官期間,做驅虎文驅虎的事跡。又如“張任初為指揮僉事,驍勇有才略,嘗遇虎踞林鳴吼,眾莫敢攖,任持槍刺殺之”,[47]講述軍事指揮官張任殺虎的故事。皈依于佛教和道教的人往往被視為沉穩、智慧、通神、有感化和感召力的象征,因此僧道應對虎患的方式以道德感化為主。如平壩高峰山寺所在之處“山多虎害,自立剎后,虎乃潛逸”。[48]再如,“釋廣能,號德彬,正統間卓錫月潭寺戒行,勤苦讀書誦經,有虎入寺,僧眾驚走,能不為動,虎徐去。”[49]記載了僧道們用感化驅虎的事跡。綜上,可以看出明代貴州作為歷史開發的高潮期,人虎爭地等人為、自然因素引發的虎患成為中后期的一種常態,使得驅虎、捕(殺)虎成為一種必然,形式也更加多樣和復雜化。官方和民間的應對基本持平衡狀態,以虎傷人、人被動應對為主。
四、結論
本文從環境史視野對虎患進行考察,其立意在于還原特定時期特定地域特定的人與動物關系事實,對明代貴州地區典型的人虎沖突現象——虎患進行了梳理、復原,屬于階段性工作。歷史文獻記載表明,隨著區域開發活動的不斷展開與深入,明代貴州地區的虎患現象在早期較少且烈度低,至中后期(以正統、嘉靖、萬歷年間為主)爆發頻繁且愈益酷烈,多發區域集中在丘陵山地地帶的東部、中部地區。針對虎患發生的不同時間、地點、烈度及受害人,其社會應對以民間、官方和僧道三個群體為主,應對方式則主要有祈禱、捕殺、感化三種。
關于虎患背后的更深層次驅動因素分析,還需要在未來的研究中繼續探索。歷史時期,限于時代條件和社會發展水平,在人類的認識里,大型食肉動物向來與人為敵。為了生命安危,人類與動物彼此傷害。從歷史事實出發,基于生存需求,人類文明的演進是以部分生物的減少或滅絕為其代價的。而珍惜善待動物資源與環境,彌補前人在歷史時期為逐利而過度殺戮的過錯行為,防止類似悲劇再次發生,是人類當前的重要責任。只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才是真正的生態文明。
[參考文獻]
[1]曹志紅.虎種中國起源說的學術史述略[J].文教資料,2015,(26):78-80.
[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4年簽發的《關于印發貴州省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建設實施方案的通知》(發改環資[2014]1209號)[EB/OL].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
[3]郭鵬.漢中虎跡[J].大自然,1988,(2):15-16.
[4]陶喻之.漢中歷代虎患鉤沉[J].漢中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3):47-54.
[5]李天培.漢中史料中的虎跡[J].野生動物,1998,(5):40-42.
社會科學方向評職知識:社會科學類論文哪里投稿發表快
社會科學方向工作人員在晉升職稱時要發表論文,但是他們往往不清楚哪里投稿比較快,小編在此介紹:能接收社會科學論文刊物有很多,但是如果作者自己盲目投稿,發表周期是比較長的,因此建議大家多咨詢專業機構,只有在他們的幫助下投稿才比較快,期刊之家發表論文經驗是非常豐富的,需要發表論文的作者可以咨詢我們的編輯老師,幫助您快速投稿。
SCI論文
- 2023-07-06博士有SSCI期刊發表論文經歷重要
- 2022-11-10ssci從投稿到發表要多久?
- 2024-04-01ANNALS OF PHYSIC最新分區是幾區
SSCI論文
- 2023-08-24論文發表多久可以被ssci收錄
- 2023-06-14發ssci論文能查到嗎查詢流程
- 2023-12-25AHCI發表論文算學術成果嗎
EI論文
- 2023-06-28ieee xplore 是ei檢索嗎
- 2022-12-07ei期刊論文發表有難度嗎
- 2023-02-07ei會議提前多久開始征文
SCOPUS
- 2023-03-28scopus收錄哪些學科的期刊
- 2023-03-20scopus高級檢索功能怎么用?
- 2023-04-12scopus數據庫收錄哪些門類的文獻
翻譯潤色
- 2023-05-11生物醫學sci論文潤色有用嗎
- 2023-05-06基因測序文章怎么翻譯潤色
- 2023-05-09鍛造相關中文文章怎么翻譯為英文
期刊知識
- 2020-08-05sci論文怎么修改
- 2015-06-05發表宗教類文章的核心期刊
- 2022-04-02論文三版起發需要寫多少字
發表指導
- 2022-03-15留守兒童教育已發表過的論文
- 2018-03-17審稿快的生物類核心期刊多久可以
- 2020-07-28臨床麻醉論文發表選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