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論文《墨子》研究中援墨注儒現(xiàn)象
時間:2016年10月31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shù):
這篇古代文學論文發(fā)表了《墨子》研究中援墨注儒現(xiàn)象,援墨注儒現(xiàn)象即為清以前《墨子》研究的主要特色。論文探討了戰(zhàn)國至秦漢間的《墨子》、唐宋辭章之儒看《墨子》以及明清時的援墨注儒,由于乾嘉學人固守儒家的正統(tǒng)思想,很難跳出援墨注儒的藩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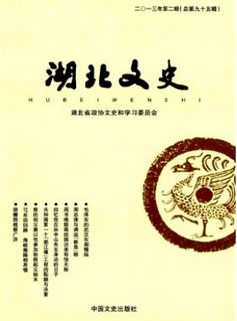
摘 要:春秋戰(zhàn)國,儒墨頡頏,百家爭鳴。即使是在《墨子》興盛一時的戰(zhàn)國,《墨子》研究亦未完全脫離援墨注儒的藩籬。儒學為宗,《墨子》絕而不息,牢固的儒家正統(tǒng)觀念更使得后世的《墨子》研究者很難跳出援墨注儒的窠臼。以致于后世學者立足儒家學說,看墨必提儒、說墨必比儒,贊墨必贊儒。
關(guān)鍵詞:古代文學論文,《墨子》,援墨注儒,儒墨關(guān)系
《墨子》研究,淵源流長。李光輝認為,關(guān)于《墨子》的評說及研究在戰(zhàn)國就開始了[1]。豪舍尓說:“觀念史力求找出(當然不限于此)一種文明或文化在漫長的精神變遷中某些中心概念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過程,再現(xiàn)在某個既定時代和文化中人們對自身及其活動的看法。”[2]按照這種方法論的要求,我們即可以逐一離析出《墨子》研究的核心觀念,并與一個時期社會與文學的發(fā)展歷程相互印照。
一、戰(zhàn)國至秦漢間的《墨子》取舍
春秋以降,大道廢弛,諸侯以百姓為芻狗。王室衰微,大國爭霸,士民階層形成。劇烈的社會變革對學術(shù)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統(tǒng)治者的提倡,各種學派紛紛出現(xiàn)。各派各家都著書書立說,廣授弟子,參與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滲透,學術(shù)思想極為繁榮。儒、道、墨、法、陰陽、名、兵、農(nóng)、雜、縱橫各家在戰(zhàn)國可謂爭奇斗艷,百家爭鳴。
墨家致力于民之倒懸,安頓惶惶人心,弘其道而忘其身。由于年代久遠,戰(zhàn)國時期,研究《墨子》的著作除了僅有的魯勝《墨辯注》已亡佚外,專門著作鮮見紙端,只是散見于諸子散文(包括序跋)中。這一時期,贊墨者少,且淺嘗則止,多為零碎的議論,《墨子》研究處于沉寂之中。熊鐵基指出,漢初道家由批判儒墨變成了“兼儒墨,合名法”[3]。可見,諸子之間雖然各取所需、各施其長,但他們之間的聯(lián)系也密不可分。《漢書·藝文志》說“其言雖殊,辟猶水火”,但相滅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孟子雖對墨子的做人立場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卻站在儒家立場上對墨家的主張嗤之以鼻,認為墨家所謂主張“兼愛”即為“無父”,為“禽獸也”。荀子更是對《墨子》不屑一顧。《荀子·非十二子》中認為“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quán)稱,上功用、大簡約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铏也。”反對墨子“僈等差”(《王霸》),“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
反對墨家“自為之然后可”,《天論》攻擊墨家“有見于齊,無見于畸”,《解蔽》反對墨家“蔽于用而不知文”,《富國》篇則批判“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認為“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jié)用‘也,則使天下貧”。對墨家非樂的主張進行專門批駁;又如《韓非子·顯學》評說儒墨術(shù)等流派及儒墨喪葬之說優(yōu)劣等;解釋建立在對墨家相關(guān)學說進行研究的基礎(chǔ)上。因這些觀點都出于援墨注儒的立場,故這些學說往往從儒家角度評述墨子及墨家,或只為一定目的“執(zhí)其一端”,這種立場和方法客觀上更加深了儒家思想的滲透和影響,也從側(cè)面顯示了諸子百家對墨家思想及其社會作用研究不足,說明墨家當時已開始游離于正統(tǒng)思想之外。《史記》言墨家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4]。《墨子》尚武任俠,講信重義。秦漢社會,此風尤盛。有學者認為,無論是靠武力征服六國的秦國,還是高祖以武力定天下的漢初,朝中重臣亦皆是行伍出身,全社會彌漫著尚武習氣。即便是文人,也是“讀書擊劍,業(yè)成而武節(jié)立”,“秦雖鉗語,燒詩書,然自內(nèi)外薦紳之士與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無所懼。”[4]秦的高壓文化政策并未阻止墨家的發(fā)展及傳播。
秦短祚而亡,諸子俱損,援墨注儒雖無從談起,但《墨子》卻在各種學說中變相傳播。篤信黃老的竇太后尸骨未寒,儒術(shù)即被漢儒推為至尊,漢初“除挾書令”(《漢書·惠帝紀》),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山東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間,講義集論,著書數(shù)十篇。”(《鹽鐵論·晃錯篇》)從漢初景象即可看出,《墨子》在民間仍薪火相傳,不僅沒中斷,且司馬談在論六家之要旨時指出“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jié)用,不可廢也。”足以證明《墨子》及墨家作為漢代六大學術(shù)之一的重要性。賈誼在《過秦論》中言“非有仲尼、墨翟之賢”,秦后首次將孔墨并稱,可知,《墨子》在漢初學術(shù)流變中實際上是在其他學派體系中實行了思想流傳,與其他學說共同構(gòu)造了漢初的主流思想,其實是《墨子》的變相發(fā)展。正如蒙文通所指出的那樣:“凡儒家之平等思想,皆出于墨……儒家之義,莫重于明堂。班固言’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清廟者即明堂也。知明堂之說,創(chuàng)于墨家而儒者因之。凡儒者言禪讓,言議政,言選舉學校,莫不歸本于明堂,其為本墨家以為說,不可誣也。墨家非樂,而六藝佚《樂經(jīng)》墨以孝視天下,而儒者于漢獨尊《孝經(jīng)》,是皆秦漢之儒,取于墨家之跡,斯今文說者實兼墨家之義。”[5]此種諸學皆出于墨的論點,使得《墨子》在儒家經(jīng)義的背景下受到了重視。
二、唐宋辭章之儒看《墨子》
隋唐是大統(tǒng)一的格局。到唐朝,戰(zhàn)國時期那種國分裂、大動亂、人辯論的政治環(huán)境沒有了,對于《墨子》的研究就更顯得客觀與中庸。雖然很多士人研究《墨子》,但亦為援墨注儒的變例。從趙蕤對《墨子》在內(nèi)的諸子各家學說的普遍認同,即可看出,唐初社會的開放和思想的解放給文人士子提供了很大的空間。趙蕤引墨子“節(jié)用”論以批評當政者奢糜不恤民情,與魏徵編輯《群書治要》主旨相同,即為統(tǒng)治者施政提供理論借鑒,客觀上鞏固了儒家的文化統(tǒng)治。他在《長短經(jīng)》記有“神農(nóng)形悴,唐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墨翟無黔突,孔子無暖席,非以貪祿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人之害。”[6]對墨家的獻身精神給予很高的評價,趙蕤這種把墨儒等同對待的態(tài)度,使得儒家與墨家皆為其所用。
唐儒韓退之開啟“儒墨為用”的千年論爭,不僅是墨家思想雖絕猶存的證明,也把援墨注儒推向了高潮。援墨注儒不僅抬高了墨家的主張,也把儒學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它表面上試圖調(diào)和儒墨,實際上使儒學的內(nèi)容更為廣泛,使得《墨子》成為闡釋儒學的工具。韓愈承漢代“儒墨并舉”、“孔墨同稱”的傳統(tǒng),一篇《讀墨子》①讓其備受批評與爭議。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圣,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cè)缡窃?余以為辯生于末學,各務(wù)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僅就《讀墨子》一篇或許還難以了解韓愈對《墨子》的全面態(tài)度。《與孟尚書書》中道:“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于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于已壞之后,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由此可以斷定,韓愈在《讀墨子》一文中所主張的“孔墨相用”實意在說明:儒墨之辨,實“生于末學,各務(wù)售其師所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韓愈的這種崇儒排墨的思想其實在其他文章中也有表述。如《上宰相書》有曰:“僅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農(nóng)工商賈之版,其業(yè)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圣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jīng)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之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諛佞诪張之說,無所出于其中。”“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于其心”亦表明其對儒墨家的立場。而且在《問進士策》里,韓愈亦以“夫子既沒,圣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辟之”表明了儒家立場。此外在《送王秀才序》中亦謂:“夫沿河而下,茍不止,雖有遲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圣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觀圣人之道,必字孟子始。”《送浮屠文暢師序》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如果之前儒墨同用乃明智,“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韓愈把它“取以為法焉”,這就有點不正常了。更何況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游天下,目的也只是“詠歌其所志”,與儒家讀書報國的心理如出一轍。
然而后人對韓愈的評述更讓人無可奈何、甚至啼笑皆非。程頤寫道:“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論不知謹嚴,故失之。”[7]歐陽修站在儒家的立場上言道:“然其強本節(jié)用之說,亦有足取者”[8],算是客觀之說,然后世之評說就有失公允。首先黃震否定了韓愈之說,“墨子之尚同,謂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與孟門所謂如其不善而莫違之違正相反。”“墨子之言兼愛,謂法其父母與法其君皆為法不仁,當法天。與孔門所謂孝弟為仁之本者正相反。”“愚曰:孔子不必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9]馬端臨亦在《墨家考》中說:“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尚賢尊德,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之。”認為墨翟之言華而不實,“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者”,并建議“深鋤而力辯之”[10],他對墨家的學說持一種懷疑的態(tài)度,表現(xiàn)出一種儒家衛(wèi)道士的立場。朱熹更甚,在《墨子》中斥道:“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矯偽,不盡人情而難行。孔墨并用乃是退之之謬。”[11]對墨子惟恐避之不及。高似孫《子略》言:“墨之為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不辟可也。惟其言近乎偽,型近乎誣,使天下后世人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不可以不加辟也”[12]。王令亦言:“墨翟固有罪”,“天下之大害者”[13],在援墨注儒的基礎(chǔ)上,甚至壓墨揚儒。欒調(diào)甫說:“《墨子》書自漢以來,已不甚顯聞于世。宋元而后,益弗見稱于學人之口”[14]總之,宋儒雖然不避談《墨子》書,但其“辟墨”思想?yún)s是顯而易見的,雖然他們評墨已趨于平心靜氣的學術(shù)分析(如朱熹、歐陽修等人),對于《墨子》中的思想和楊朱已區(qū)別對待,但援墨注儒貫穿于宋儒研究《墨子》的始終,闡釋《墨子》即為援墨注儒的目的始終未變。
三、明清時的援墨注儒
明代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使得個體生產(chǎn)者成為社會上活躍的經(jīng)濟主體,經(jīng)濟上的自足引發(fā)了精神上的自覺,他們迫切需要一種思想和學說來代表本階級的利益,而墨子提倡的平民意識等一系列主張正是代表著“農(nóng)與工肆之人”的利益,市民階層的不斷壯大,為《墨子》的重新振興提供了強大的階級基礎(chǔ),是《墨子》再度復興的重要條件。張翰在他的《松窗夢語》中,描述當時商賈販夫,“同欲而共趨之,如眾流赴壑,來往相續(xù),日夜不休。”“追逐錨株之利至富的情狀:財利之于人,甚矣哉……雖敝精勞形,日夜馳鶩,猶自以為不足也”[15]。大量書籍被印刷和出售,客觀上促進了書籍的傳播,《墨子》一書也是其中的一種。據(jù)鄭杰文考證,自正統(tǒng)年間《道藏》之《墨子》由張宇初編纂以來到崇禎時金堡、范方等評點《墨子》,在276年間,有文字記載的《墨子》刊、校、注、研究等著作共計28種。由于明人刊刻的序跋、評點較多,所以刊刻業(yè)的發(fā)展客觀上促進了《墨子》研究的拓展與深入[16]。明萬歷進士第一名、著名思想家、文獻考據(jù)學家焦竑在《墨家小序》中認為:“墨氏見天下無非為我者,故不自愛而兼愛也,此與圣人之道兼濟何異?故賈誼、韓愈往往以孔墨并名。然見儉之利而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殊不親,此其弊也。”[17]焦竑有專門討論義利關(guān)系的文章寫道:“自世狠以仁義功利歧為二途,不知即功利而條理之乃義也。……一厚農(nóng)一足國,桑大夫蓋師其余意而行之,未可以人廢也。藉第令畫餅癖饑可濟于實用,則賢良文學之談為甚美,庸柜而必區(qū)區(qū)于此哉。”[18]對于義利問題,焦竑否定了墨家公利大于私利的主張,贊揚儒家義利并重才能使天下安定的思想。對儒家經(jīng)典《易》將義利并提,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并舉了桑弘羊義利并重,輔佐武帝厚農(nóng)足國的例子。指出施行墨家主張的后果是“取貧民則公利薄,而民去其業(yè)”。
對于《墨子》中的主張,宋濂持批駁的態(tài)度,“墨者,強本節(jié)用之術(shù)也。……孔子亦曰:奢則不遜,儉則固。然則儉者,固孔子之所棄乎?或曰,如子言,則翟在所取,而孟子辭而辟之,何哉?曰:為有二本故也。”[19]他認為孟子之所以棄墨是因為儒家中已有“二本故也”。相對于宋濂,陸穩(wěn)的取舍恰相反。明嘉靖三十二年唐堯臣刻本,陸穩(wěn)敘述了自己認識《墨子》的歷程。他認為墨子“非圣人類也”、認為賈生“特言之過耳”,對韓愈謂其道與圣人相為用甚“疑焉”。他認為墨子之道“果異于自私自利之徒”,并認為墨子“其言足以鼓動天下之人尊而信之”,孔孟并稱,“宜也”。他批評孟子,出于孔墨之后,“孤取天下之所尊信者辟而絕之,得無防其流歟?”[20]這與李贄反對傳統(tǒng)思想,對《墨子》加以贊揚不謀而合。
相比陸穩(wěn),李贄與胡應(yīng)麟的評說有點激烈。李贄認為墨子的救世主張是對的。“明言節(jié)葬,非薄其親而棄之溝壑以與狐貍食也,何誣人,強人入罪為?儒者好入人罪,自孟氏已然矣”[21]。對于孟子辟墨給予諷刺抨擊。胡應(yīng)麟則認為墨家異于儒家,是因為要爭一席之地,標立意,立心說。他認為《墨子》“蓋其意欲與吾儒角立并驅(qū),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統(tǒng),故肆言以震撼一世,而冀其徒。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馴至儒墨之稱雜然并立與衰周之世”[22]。汪中表達的觀點在當時是最有反儒色彩。他認為墨子所倡學說與禹相同,并非“墨子背周而從夏”,并認為“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于’不相為謀‘而已矣。”并對墨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23]給予了極高的贊賞。針對此種“不倫不類”,翁方綱諷刺攻擊道:“有生員汪中者,則公然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之言’兼愛無父‘為誣墨子,此則又名教之罪人,又無疑也”[24]。散文家兼詞人的張惠言則認為墨子影響系“炒作”之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雖他說悖于常理,不安于心者,皆從而則之,不以為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25]。
此外畢沅在《墨子敘》中亦曰:“世之譏墨子,以其節(jié)喪、非儒說。墨者既以節(jié)喪為夏法,特非洲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對墨家的非儒說進行批評,并嘲諷“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為孔子之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26]。這也是后世學者批判畢沅《墨子敘》的理由,即好以儒言附會。畢沅說與孫星衍不謀而合,孫在《墨子后序》中也表達了孔墨同出,且墨高于孔的思想,并對司馬遷、班固等人對墨子的理解給予批正[27]。對于司馬遷與班固“皆不知《墨子》之所出”,只有淮南王知之,“’墨子學儒者之業(yè),習孔子之術(shù),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墨子有節(jié)用,節(jié)用,禹之教也。”[28]對于孟子批評墨子予以反擊,評說還算中允。雖此四人為弘揚墨子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但畢竟是辭章之儒,他們的對儒墨關(guān)系的理解也流于表面,至多只能表達對墨子的敬意。
被認為闡釋《墨子》比較大膽的汪中亦是如此。他只是把墨子作為一個解釋經(jīng)書,證明事例的工具,校注《墨子》時往往使用經(jīng)書的路數(shù)來穿鑿附會,如此以來難免錯漏較多。這在清代學人的著作中多有評述,此不贅述。汪中雖然讓沉寂的墨子及《墨子》暫時受到了重視,但孔墨在汪心中地位高低不言而喻。汪中雖給予墨子極高贊賞但亦未跳出援墨注儒的窠臼,更遑論張惠言等人了。清軍入關(guān)后,雖然仍是孔儒獨尊,但由于士人遠離政治與民族意識的討論,文人們主觀上遠離政治,他們著書立說,漸漸走上了循經(jīng)求義的路子。不僅如此,晚清孔孟之學受到公開批判后,為了從傳統(tǒng)學術(shù)中發(fā)掘救國良策,一些學者結(jié)合西方近代研究方法,對《墨子》中的自然科學、社會政治思想學說進行歸納、分析和綜合[29-30],此種背景下《墨子》研究的發(fā)揮經(jīng)義亦成為《墨學》研究史上一大特色之一。
推薦期刊:《湖北文史》是湖北省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辦,被中國學術(shù)期刊(光盤版)全文收錄期刊收錄,是省級期刊。
SCI論文
- 2024-09-14醫(yī)學sci論文發(fā)表全攻略
- 2024-09-14sci論文快速見刊方法分享
- 2024-09-14sci論文添加作者理由模板
SSCI論文
- 2024-09-02精選ssci收錄文學類期刊15本
- 2024-08-31SSCI論文第一作者是什么分量?
- 2024-08-23藝術(shù)方面論文發(fā)核心容易嗎
EI論文
- 2024-09-13數(shù)據(jù)挖掘方向EI會議推薦
- 2024-09-12被ei收錄的學術(shù)會議是什么意思
- 2024-08-23力學領(lǐng)域ei會議或期刊
SCOPUS
- 2024-05-29scopus收錄哪些管理類期刊
- 2024-05-09管理學發(fā)一篇scopus論文難嗎
- 2024-04-15SCOPUS檢索的會議怎么找
翻譯潤色
- 2024-08-17國際中文期刊投稿后多長時間見刊
- 2024-08-17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 2024-08-17環(huán)境類外文雜志推薦
期刊知識
- 2024-09-10園藝學科核心期刊目錄
- 2024-09-06一類二類三類四類期刊分別指什么
- 2024-08-27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幾個版面
發(fā)表指導
- 2024-08-17論文允許拆開發(fā)表嗎
- 2024-08-17注冊會計師寫論文寫什么方向
- 2024-08-17論文題目怎么算新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