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雜志發表網哲學在終結處開端
時間:2015年12月10日 分類:推薦論文 次數:
本篇文章是由《南方文壇》發表的一篇文學論文,歷時六屆的《南方文壇》年度優秀論文獎已被專家認為“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一項重要獎項”。還有已歷時五屆的與《人民文學》雜志聯合舉辦的“中國青年作家批評家論壇”,每年10月舉行,5年來已經成為中國青年作家和批評家的重要對話交流活動和品牌論壇,被認為是一年一度的“華山論劍”,在文壇聲譽日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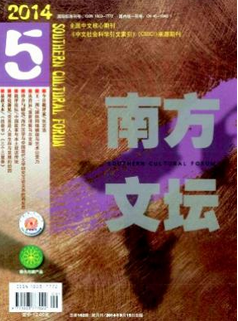
雷 天:今年一月圖書訂貨會上,您主編的解釋西方文化中最主要的102個觀念的《西方大觀念》(華夏出版社,2008年1月),受到了廣泛關注。有兩個問題我想請您再稍做解釋:第一,102個觀念的選擇標準是什么?第二,與《不列顛百科全書》和《人類思想的主要觀點——形成世界的觀念》相比較,《西方大觀念》在詞條解釋方 面有什么特別之處?
陳嘉映:《西方大觀念》是大英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的六十卷本叢書《西方世界的偉大著作》的頭兩卷。《西方世界的偉大著作》選了西方歷史上文科的主要著作,包括少量自然科學著作,而頭兩卷是用其他58本書里所討論的內容總結出的102個大觀念。它和《不列顛百科全書》《人類思想的主要觀點——形成世界的觀念》在性質上的差別還是蠻大的。
在詞條解釋方面,《西方大觀念》也有特點,比如解釋因果性概念,就是講因果性出現在西方偉大著作中都有哪些形式,前人都有哪些觀點,是概述性的。這樣能起兩個作用,一是可以知道西方思想史主要觀念,關于這些觀念最基本的說法和角度。二是有索引功能,講到某一個觀念,后面列了非常詳細的索引,幾乎可以找到到西方重要著作中和這個觀念有關的主要論述。
雷 天:有點像思想史的考察。
陳嘉映:對,是思想史的概述和索引。 哲學究竟反省什么
雷 天:因為去年讀了您的《哲學 科學 常識》,所以我在查閱《西方大觀念》的時候,還特意查找了這三個詞條,“哲學”詞條是您翻譯的,“科學”詞條是您和孫永平教授翻譯的,沒有“常識”這個詞條。您在《哲學 科學 常識》開篇引用的老子“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意思是指母為常識,子為哲學-科學,還是指母為哲學,子為科學?
陳嘉映:當然“母”是常識。我更愿意說是“自然理解”,就是我們自然而然理解一件事情。
雷 天:科學、哲學都是我們從自然理解生發出來的?
陳嘉映:對。
雷 天:“復守其母”是什么意思?
陳嘉映:我想,對當代有知識有文化的人來說,不懂科學,既不可能也不應當,我們肯定在一定意義上知道科學。在這種情況下“復守其母”,是說科學在某種意義上是最先進的認知方式,雖然對我們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我們全部真理,甚至可以說不是根本的真理。我希望提醒讀者警惕“唯科學主義”的傾向。
雷 天:您在《哲學 科學 常識》里認為,今天的哲學不可能以建立普適理論為目的,以建立普適理論為目的的哲學已經終結,現代哲學應回到出發點,以理性態度從事經驗反省和概念考察,以期克服常識的片斷零星,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更為連貫一致的理解。但您所說的哲學在經驗反省方面的任務好像跟科學有一些重合。能否先請您解釋一下,哲學反省什么樣的經驗,以及對何種概念進行反省?
陳嘉映:這個問題挺好,這本書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先回答最后一個問題。
我相信我在用“經驗”這個詞的時候,是一個比較合適的用法,我并不認為一般被稱作自然科學研究的工作是對經驗的反省。這一點是跟哲學不一樣的,它不是對經驗的反省,當然有人——哲學家們有時把自然科學叫做“經驗科學”,但我在書里強烈表示經驗是容易誤導的,叫“實驗科學”可以,叫“實證科學”也可以,雖然是一個名號,但叫“經驗科學”誤導得太厲害,最好不用。我舉一個例子說明實證科學并不是對經驗的反省。
比如說,在生活中會碰到很多義務和愛情發生沖突的時候,小說里描述得更多。討論這些沖突怎么來的和怎么解決這些沖突,都屬于經驗反省的范圍,不是科學處理的對象,而科學所處理的都帶有普遍機制,并不反省我們的經驗。
哲學是反省這些經驗的。我說的概念考察就是這樣,比如說我們經常討論這樣的問題:怎樣生活得更快樂,怎樣生活得更幸福。那么當然要問快樂和幸福是什么關系,以及什么才叫幸福,錢多是否一定幸福?這些問題基本就是哲學問題,只不過哲學可能更注重討論其中帶有普遍性的概念,比如說像“快樂”和“幸福”這些概念本身,而不是討論個案。
雷 天:您在書上特別強調這一點:哲學不是從現象進步到現象背后的機制,而是從現象退回到關于現象的陳述,退回到我們的概念方式……哲學的任務并不是脫開我們的概念來揭示世界的“客觀結構”。您能否把這個意思解釋得更清晰一些?
陳嘉映:這些說法都是從維特根斯坦那里搬過來的。我再舉個例子,還是剛才提到的快樂。關于快樂不快樂,快樂和幸福是什么關系?人能不能以苦為樂?吃喝玩樂的快樂和圣徒的快樂有沒有共同點?我們能不能知道別人是否快樂,或魚是否快樂?這些都是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回答這些問題時需要考察的是,我們在哪些情況下會說到快樂;我們能不能說、為什么說苦行僧也有他的快樂;如果我們說:他現在真快樂,那我們是怎么知道他快樂的呢?抑或我們永遠只是在猜測他的心理?如果不可能有正確的答案,猜測還有什么意義呢?諸如此類的問題,在維特根斯坦那里就是“退回到關于現象的陳述,退回到我們的概念方式”。但現在不少人會以為,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神經系統,研究內啡肽的分泌等等。我追隨維特根斯坦,認為這些完全是另外一個層面的研究,無助于我們澄清概念。我說“無助于”,很多人會不同意,但這里無法更進一步討論了。
雷 天:您能不能把哲學需要反省的概念歸個類?
陳嘉映:這也是一個好問題。我們平常說話的時候是在描述這個世界,談論這個世界,在我們的談論中有一個特殊的部分,那就是講述道理。比如說,我讓你做一件什么事情,你不愿意做,我想辦法說服你,就要講個道理給你聽。在講道理的時候就會使用一些概念,像主觀、客觀、事實、真理、真、虛偽這些詞。我把這些在講述概念中最常用的詞,叫做論理概念。
雷 天:您的意思是,這些概念構成了我們思考基礎?
陳嘉映:構成我們思考的基礎和論理的概念。說“思考的基礎”可以更通俗一點,但我認為用“論理概念”更好一點。比如講故事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思考,比較麻煩,不是那么清楚,而論理概念雖然聽起來不是那么通俗,但比較清楚。我的意思是說,哲學所要反省的概念主要是這些論理概念,用你的話就是構成我們的思考基礎的概念。 如何閱讀古典哲學
雷 天:一般我們說起哲學的時候會想起哲學的本質是“愛智”,也會想起把哲學從天上請回人間的蘇格拉底的名言:未經省察的人生不值得過。哲學家施特勞斯就特別強調蘇格拉底的這次“政治哲學”轉向,這種解讀也影響了很多讀哲學的年輕人。您比較強調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我想問,古典哲學對我們今天還有意義嗎?您覺得該以何種角度來閱讀和思考古典哲學。比方跟著柏拉圖去思考正義、善,或者跟著奧古斯丁去思考和接近信仰。
陳嘉映:在蘇格拉底之前,自然哲學是主流,到蘇格拉底,他說自然哲學不是他的關心所在,他關心的是人的生活。一般希臘哲人談到跟人相關的事情時,幾乎都是和政治相關,當然這個詞翻譯成政治本身也會有問題,要回到希臘去看,因為希臘是一個男性公民的社會,個人跟城邦的關系非常密切,城邦在一定程度上規定著一個人之為人。既然從自然哲學轉向對人的關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有政治哲學轉向也可以。哲學中的語言轉向,我傾向于把它翻譯成為語言轉向,而不是語言學轉向。這和政治哲學轉向沒有可比性。我對20世紀西方哲學研究的多一點,我個人認為,語言轉向有比較深刻的意義,在這本書里,我也試圖把語言轉向和西方哲學史、西方科學的發展聯系在一起來看待。
雷 天:施特勞斯比較強調閱讀古典哲學文本時要從文本的字里行間讀出微言大義,強調哲人的隱微術。您在閱讀這些古典哲學文本的時候會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和角度?
陳嘉映:隱微的讀法,就像是古人用的春秋筆法。劉小楓主編的書里就有一本《修昔底德的春秋筆法》。現在有人提倡讀中國古典,有人提倡讀西方古典,各有各的讀法。我不相信有唯一最好的讀法。每個人的文化水平不同,要做的事情不同,怎么會一種讀法適合所有人呢?于丹、易中天面對的是一種讀者,劉小楓面對的是另外一種讀者。但你說是不是一定就是劉小楓那個高呢?至于說隱微的讀法,我個人不太相信,讀出希臘語中的隱微不是我們的能力所在。雖然我不贊成隱微的讀法,但并不是說不能有這種說法。其次,即使隱微的讀法不是最好的,但我們對古典著作的讀法不能只是通俗的,通俗是要有源頭的,這個源頭就在于一些肯下死功夫的學者。這些人做事情的面可能很窄,但是那么一點點研究他也下了很多功夫做。普通人了解古典就要讀這些下功夫的人的書。
雷 天:您自己會采取什么樣的角度讀類似《理想國》《懺悔錄》這樣的哲學書呢?
陳嘉映:雖然我的古文不好,但希臘文幾乎不會,比較之下,我讀中國古文的時候就好一點,還可以有自己與眾不同的看法。比如說讀李零的《喪家狗》,雖然李零對古典比我熟很多,對某一個注釋,我也會跟他有一爭。但是如果希臘語有一個專家說話了,我即使不同意也得認錯,沒有辦法爭。我讀希臘古典不大敢進入非常細微的文本閱讀。這點我個人做不到。 我看中國“哲學”
雷 天:您的書里談到了中國哲學,您認為中國哲學有理性,但缺乏對世界提供進行整體解釋的理論興趣。按您的說法,中國的確沒有希臘意義上的哲學、科學。您認為中國哲學僅僅是一些修身、處世、治國的道理嗎?
陳嘉映:這個事情說起來也平常,首先看你怎么界定哲學。我的意思是說,“哲學”跟“文化”一樣,一百個人有一百個回答。我認為哲學是一個從西方翻譯過來的詞,既然如此,我們就只能以西方思想為典范。
從希臘到近代,西方思想特點有很多,可以從各種角度描述,從我這本書的志趣來說,強調西方哲學對整體理論有求真的精神。一般人都愛好整體理論,很多人都能講一套東西,但對于它是不是真,就不是太感興趣。實際上,在真和好玩兩者之間經常有矛盾。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其實一般人在談到整體理論宏大觀念的時候都偏向于美的那一面,偏向于好玩的那一面,至于信不信,則不是特別在意。而西方理論傳統有一個特點,有求真的勁兒。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精神。西方哲學和近代科學的發展是跟這種精神相聯系的,中國傳統的讀書人不大會有這種精神。
那么中國哲學和中國思想還剩下些什么呢?就是修身齊家,像黑格爾說的道德箴言或者道理?我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會思考論理方式。黑格爾認為它只不過是一種道德箴言,我認為含有批評在里面,主要批評它零零星星不成系統。
問題在于“系統”是怎樣的一種系統性?《論語》東一句西一句,如果能編得系統點當然更好。但因此說孔夫子沒有系統性就有點絕對。系統有表面的系統性、有內涵的系統性。我當然不認為孔夫子只有一些道德箴言,他當然是有一個吾道一以貫之的“道”。我們讀《論語》,讀跟孔子有關的記述,可以感覺到孔子是一個有思想系統的人,雖然他的表述非常不系統。莊子也是這樣,莊子一會兒這么說,一會兒那么說,但讀下來,會感覺這個人幾乎就在眼前,非常統一。
雷 天:您的意思是中國傳統思想不能以西方“哲學”概念去定義。因為中國哲學是不一樣的系統。像老子有老子的系統性,莊子有莊子的系統性。您的另外一個意思是說,中國的思想構成了我們今天的思維世界?
陳嘉映:中國的傳統思想對我們讀書人影響就更深一些,但話不可以說得太極端。首先我非常反對把中國思想僅僅歸結為儒家。如果宋朝的學者這么說的話還有他的道理,但今天說中國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就太不能接受了。老子、莊子、墨子都是中國傳統思想。第二,我們接受西方、印度的東西,把它視作傳統的一部分沒有什么奇怪的。我們老是把自己想象成為一個純粹的中原人,實際上不一定。憑什么要廣西人把儒家認作他的傳統?如果他把儒家認作傳統,多多少少相當于我把亞里士多德認為是我的源頭一樣,有點差別,但不是那么大。再比如說佛學,是中國的文化傳統還是印度、西方的傳統呢?宋明理學反對佛學,但也接受了很多它的影響。把傳統分得一清二楚,像是要向什么東西效忠似的,我覺得荒唐。
雷 天:哲學家懷特海說西方哲學就是給柏拉圖作注腳。孔夫子在中國是不是也是這樣的地位?
陳嘉映:懷特海的話很有意思,所以就比較容易流傳。但我認為他并不是非常認真地說。我當然不認為西方哲學只是柏拉圖的注腳。我也不認為中國哲學都是孔夫子的注腳。比如像莊子,應該把他看作孔夫子完全平等的對話者。整個中國傳統,至少是士大夫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個人的對話——儒家和老莊集于一身的,以前叫出處,叫進退。這是對話的關系,不是注腳的關系。
雷 天:您是不是在中國思想上比較推崇諸子,對后面宋明的不太感興趣?
陳嘉映:就我個人喜歡來說,我更喜歡諸子,但這不是我比較推崇諸子的主要原因。我覺得,源頭的經典是最重要的經典,漢朝人讀先秦有一套讀法,宋朝人讀先秦有一套讀法,現代人學了西方的東西,生活在現代世界,讀先秦典籍也有一套讀法,肯定不可能跟漢朝人或者宋朝人一樣,差別會非常大,但源頭永遠是源頭。我認為每一朝每一代人都會對先秦感興趣,宋朝人想越過漢學讀源頭,清朝的人也想越過宋朝的東西讀源頭,人人都一樣,只是越往后就會越參照前面的讀法。
雷 天:談到參照前面的讀法,我想到一個關于“解釋”的問題。如果一個希臘文特別高明的學者跟你解讀《理想國》,是這樣說的,不是那樣說的,你可能會更相信他的說法。這有點像戴震說的,訓詁明而后義理明。
陳嘉映:對。像我們這種中層的讀書人大概就是上傳下達吧,我們注解不了什么書,對中國書、外國書寫不出很好的注本來,我們要讀這些書要靠前人。有時我出去,大家會把我當作某個小領域的專家,但我跟學生說,我不是專家,那種我們必須跟他們學的人是專家。我想用建筑來比喻專家,他們是挖地基的,辛苦的,沒人知道的,我們知道建筑是貝聿銘設計的,但誰都不知道這個建筑的具體工程力學是誰做的,更不知道打地基或者打木樁的是誰做的。這就是專家干的活。 以哲學為業意味著什么
雷 天:哲學家今天能做什么,以哲學為業意味著什么?在中國,是不是意味著三五好友討論自己共同感興趣的話題;為了生存寫一些像天書一樣的論文,針對公眾也寫一些哲普讀物。您這本書作為哲普讀物其實也不好讀。
SCI論文
- 2022-11-10ssci從投稿到發表要多久?
- 2023-07-06博士有SSCI期刊發表論文經歷重要
- 2024-04-01ANNALS OF PHYSIC最新分區是幾區
SSCI論文
- 2023-12-25AHCI發表論文算學術成果嗎
- 2023-06-14發ssci論文能查到嗎查詢流程
- 2023-08-24論文發表多久可以被ssci收錄
EI論文
- 2023-02-07ei會議提前多久開始征文
- 2023-06-28ieee xplore 是ei檢索嗎
- 2022-12-07ei期刊論文發表有難度嗎
SCOPUS
- 2023-03-20scopus高級檢索功能怎么用?
- 2023-03-28scopus收錄哪些學科的期刊
- 2023-04-12scopus數據庫收錄哪些門類的文獻
翻譯潤色
- 2023-05-06基因測序文章怎么翻譯潤色
- 2023-05-11生物醫學sci論文潤色有用嗎
- 2023-05-09鍛造相關中文文章怎么翻譯為英文
期刊知識
- 2022-04-02論文三版起發需要寫多少字
- 2015-06-05發表宗教類文章的核心期刊
- 2020-08-05sci論文怎么修改
發表指導
- 2022-03-15留守兒童教育已發表過的論文
- 2018-03-17審稿快的生物類核心期刊多久可以
- 2020-07-28臨床麻醉論文發表選刊方法